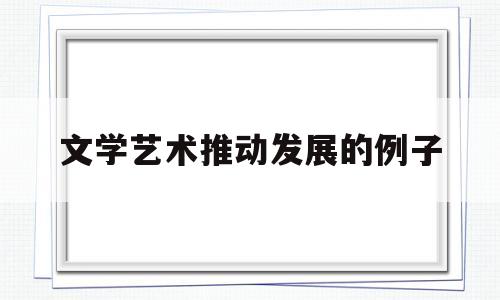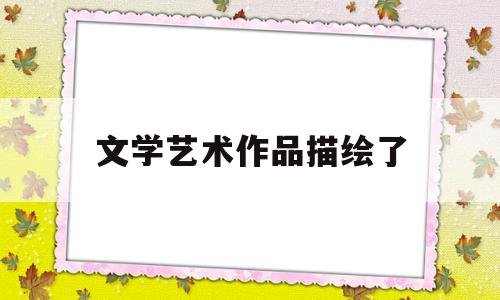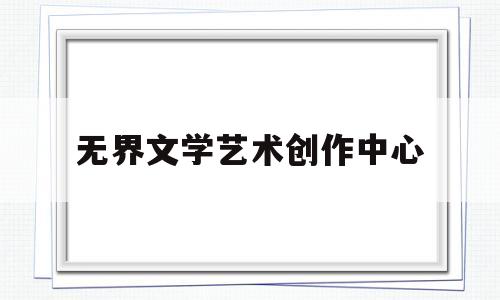八十五岁的吴式南先生(左)和九十三岁的张延彪先生同为夏承焘先生弟子
【傅国涌按:此文写于1999年夏天,是根据我在1988年前后的课堂笔记和吴式南先生发给我们的讲义整理的。今天又是教师节,想起三十年前与吴师在温州九山湖畔的问对,将此文发在这里,吴师生平著作除了去年问世的《发现艺术之美》,八十年代论文学和论语文审美教育的都还有价值,将来若有机会,应该结集出版。】
1987年,我第一次听到吴式南先生讲文学理论,内心豁然开朗,一片光明。原来干巴巴的概念也可以以那么生动的形式来表达,原来空洞的理论也可以变得如此有血有肉。我就这样走进了吴先生的文论世界。他的文论不是干燥乏味的照本宣科,而是他对生活、对人、对文学作品的心灵体验,是他长期以来对这些问题的深入思考,是从人本身出发的,充满了丰富的人性内涵,我把他的文论称为文学的人性观(也不知道吴先生以为是否妥当)。
吴式南先生1952到1954年在之江大学肢解后浙江师范学院求学,师从夏承焘、姜亮夫、蒋礼鸿、孙席珍、蒋祖怡等先生。
1957年春夏之交那场劫难降临时,他在温州师范函授部教语文,并编初中函授教材。1958年夏天还有一场余波,名为“向党交心”运动等着他,年轻、纯真、善良的吴先生,将自己思想上不通的地方和盘托出,比如对“外行领导内行”、“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这些说法。就这样被补成了右派。那年他25岁。从此,他在农村一呆就是二十年,他自称是挑了二十年的大粪。他在农村劳作之余,最感兴趣的是美术评论,尤其是研究漫画,《文汇报》曾发表他的评论《有笔如刀——评华君武画蒋介石》。他因此和华君武、叶浅予这些画家都成了忘年交,他们曾给他写过好多信,后来全都在“文革”中付之一炬。
直到70年代末,他才重返讲坛。长期的苦难而压抑的生活使他的两鬓过早地发白了,也就是在这漫长的黑暗的二十年里,他在田间地头,在昏黄的灯光下,蛙声虫鸣之中开始思考文学理论,其实他是在思考人、人性的本身。所以他所理解的文学问题,就是一个人性的问题。
回忆我的青春岁月,听吴先生在课堂上讲文论课,或者在他家里谈文学,依稀还感到温暖。
吴先生是我的恩师,他教过我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在我的生命中遭遇不幸的时刻,他曾给过我关怀与鼓励,他用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安慰我这个学生。在我的心中,他永远是一个博学、深思、有独立见解、有专业造诣的老师,一个饱经沧桑的慈祥长者,虽然时光流逝,我和吴先生也有多年没有见面了,但我的心中一直深深地思念着他。
本文的主要观点都来自我当年的课堂笔记和吴先生的讲义。
还“人性论”以光辉
长期以来我们曾经一听到“人性”二字就把它归为资产阶级的论调而嗤之以鼻。其实,“人性”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难道说无产阶级就是不讲人性的吗?这是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最大污蔑。你不讲“人性论”,难道还要讲“兽性论”吗?
人性,作为一面旗帜,的确是欧洲近代资产阶级率先举起来的,这是资产阶级为人类文明史所作的巨大贡献,已经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吴先生以充满了热情的笔调讴歌——这是一面多好的旗帜啊!我们终于从愚昧、无知的噩梦里醒过来,我们不再相信欧美资产阶级都是一些脑满肠肥、荒淫无耻、头顶生疮、脚底流脓的人。人道主义、人性论和批判的现实主义,就是他们留给全体文明人类的珍贵遗产,是两面永远金光闪闪的旗帜。
文学的核心是人性,是人性的全面呈现。文学没有国界,能够超越一切民族、阶级的界限。如果说文学有什么世界性的永恒主题,那就是人性,全面的人性。人性的旗帜就是文学唯一的也是最广阔的旗帜。就因为人类的文学中闪动着如此丰富、如此深邃的人性之海洋,文学女神才是那样百看不厌、青春永驻,既神秘又激动。在人性——人道这面总旗帜下,《诗经》与荷马,泰戈尔与但丁,屈原、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与莎士比亚、歌德、拜仑、海涅、勃郎宁夫人,普希金、惠特曼、波德莱尔和徐志摩、闻一多、穆旦,马尔克斯、海明威、卡夫卡与曹雪芹、鲁迅、沈从文、巴金.......等等文学心灵之间完全是相通的,所以我们的心灵也能为东西方的文学作品所激动。这些文学家、诗人,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时代,却有共同的语言,那就是人性的语言。他们璀璨晶莹、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都是全面人性这株长青树上所开放的奇花异卉和结出的黄金果。
吴先生对文学的理解来自他对文学自身充满血肉的观照,他提出的文学的人性观击破了黑格尔——别林斯基模式,超越了托尔斯泰、普列汉诺夫模式,也走出了我们熟悉的“现实——政治斗争——形象化工具”模式。他着眼于活的有血肉的人,着眼于人的整体内在世界,着眼于人的灵性——内在世界在外在世界中的全面折射,是真正的“人”的文学本质观。他心中的文学是活生生的,与天地、人生同呼吸、共脉搏。文学就是激荡人性、疏导人性、陶冶人性、完善人性。
以任何功利的、实用的、狭窄的眼光看文学,都是对文学本来面目的亵渎,他们是蒙在美丽的文学女神身上的一层层灰尘。而在文学女神的左右手里,各持一把人性的标尺,一把是讴歌人性的真、善、美,另一把是鞭挞人性的假、丑、恶。文学的法庭始终掌管着人类的心灵,为崇高的全面的人性而斗争,就是文学最神圣的使命。
文学的本质是表现全面的人性,也就是表现人的生命、心理、欲望、意志、理想、行动在与人的外在环境(民族、社会、时代、地域等)的相生相克中,所感发、迸射出来的喜、怒、哀、乐以及追求和抗争,爱情和创造,崇高和滑稽,庄严和痛苦,正常和扭曲等。展现的是人性的丰富多彩的不同侧面。因此他说:“文学是社会的事业,更是生命的事业。对文学的感受和评价,不只要用大脑来思考,更是要用全身心的感觉和体验。”这是心灵与心灵之间的默契,情感与情感的交融,生命与生命的拥抱,人生与宇宙的媾合。
在文学中,“情”就是“真”,即是“善”、是“美”。美国的名著《飘》(gone with the with,中译本现在译为《乱世佳人》,吴先生说虽然民族味十足,但很俗,而原题隐喻确切,传神地表达了小说的情韵)里的女主角赫思嘉的所作所为,在知上是逆历史潮流的,在行上(生活方面)是非善的,但她的人生追求、价值观念却完善地体现了:“1、必须富有;2、决不因潦倒而忧伤;3、不受任何人的支配”这一“美国精神”,是一种普遍人性的美的感情,最终又是符合于大善和大真的。所以小说才在全世界不胫而走,历半个世纪而不衰。甚至在原作者不幸逝世40多年后,还有人要从80个作家里遴选出一个女作家,以500万美元的惊人代价为之“续貂”,花三年才脱稿,以22种文字同时出版。这是人性的永久魅力,是《飘》所表达的丰富生动的人性世界造成的轰动效应。
吴式南先生从人出发,从文学本身出发,他高举人性的大旗,用一个个鲜活的例子,还给了“人性论”以光辉,还给了文学以本来面目。他常说他的文论“一切从文学的自身出发,注重于心灵的感受。自信文学乃人类的共享,学术为天下的公器,务以全人类、全天下作为思考的基准,持全方位、全开放的通达眼光。言必由衷,贵求其真;思必实证,贵求其是”。所以他的文学人性观句句都是肺腑之言,没有经院的死气、学院的迂气、取宠者的哗气、学究的奴气,这个曾经当了20年右派的知识分子,我们透过他对文学的研究也能够看到他傲然独立的人格。没有这种人格力量,他也不可能完成他的思想升华,在超负荷的劳动中,在田间地头抬起头来仰望星空——文学的、人性的星空。这是一个失去了人性温暖的人在没有人性的年代里对人性的渴望和呼唤。
四大古典小说:全面人性的例证
什么是人性?全面的人性是什么?到底有没有共同的人性?这本来是一个并不深奥而十分明白的问题,只是由于过去理论界的封闭和对左的政治路线的屈从,把它人为地划为禁区,以至幽闭了作为人的应有的起码的良知。
人性是人的客观存在,人性就是人的存在的“现实”。人如无人性,与动物何异?人是生命和肉体之身,与天地万物同构,自然有生物性、自然性(永远都无法泯灭)。生命、肉体、生理、心理就成为人之自然因素。人又是社会的细胞,群体中的一员,他必然有理想、道德、实践、创造等要求,人的社会性、理性自然也是永不泯灭的。如果说人是“生物、心理、社会”的合一,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性(含生命、肉体、心理、欲望)与人的社会性(含道德、理想、实践、创造)的合一。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五种根本需要画成一个金字塔形的五步台阶:最低的是生存的需要(包括安全、饮食),然后是爱情、友谊、荣誉等的需要,最高层次是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五个层次,其实也就是人的全面人性的具体表现,无论帝王、总统还是乞丐、流民,无不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的一切斗争,人与人之间的一切纠葛,一个人的命运所遭际的悲欢,一个性格所产生的优和劣、常和变、光辉和扭曲,都跋涉在这个五级人性台阶上。
所谓具体的人性,也就是人的这种全面普遍的人性要求在一个具体的时代环境、民族环境以至家庭环境、地域环境中的相生相克、千姿百态及其无常变化。所以,人性自身是一个恒量结构,但他在实践中却又是一个变量的形态。一方面人性是永不泯灭的,另一方面人性又无限丰富。
伟大的文学作品就是同时展现了人性的这两个量值之间既错综又平衡的情况,凡是表现了全面人性的作品,总是有着它自身固有的生命,因为它是“人”的文学;凡是远离人性的作品,即使暂时如何走红,到头来总是纸花纸人,朝生而夕死的。人类文学的长廊无非就是一系列表现全面人性的画廊。阴阳两气相合相克构成宇宙与万物的本原,这是天地万物的大道,而自然性和社会性这两大基本特征的相辅相克则构成了人性的本原,也是人性的大道、文学的大道。
千古流传的中国民间四大传说(白蛇传、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家女)为什么会如此有口皆碑、百看不厌,赢得东方人乃至全世界的喜欢呢?最根本的原因,无非在于它们都以一种超人间的传奇性的力量(包括环境)表现了普遍人性中基本冲突:爱情与压迫,欲望和抑制,理想和现实,命运和不屈,善良和邪恶......之间通过非人的幻想力量所进行的曲折斗争和胜利。
什么是天理?古人说天理就存乎人欲之中。俗谚:一天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佛云:人有七情,喜怒哀乐爱恶惧。这两个“七”字正是最质朴最明白地概括了最普遍最大量最起码的人性要求。这是文学发生的基元。文学,人类的文学创造,正是在一种现实——非现实的幻境中发射了、满足了、升华了人的这种全面的人性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有个清代人曾说文学(小说)与男女、饮食是“鼎足为三”,未为过也。
再看中国的四部家喻户晓、老幼喜爱的传世小说,它们最基本的价值,只有在全面人性的典型表现这个根本点来看,才能找到最佳的阐释。以人性为标尺,拿这四部小说与人的生命历程相参照。《西游记》代表了人性的童年、少年时期的天真和幻想,放诞和浪漫;《红楼梦》代表了人性之青年时期对爱情和婚姻问题的激动和思考,狂热和追求;《水浒传》
代表了人性之中年时期的血气方刚和爱爱仇仇、雷厉风行;《三国演义》则代表了人性之中、老年时期的成熟和权术、智慧和争斗。《西游记》和《红楼梦》还共同探索了人生之终极皈依问题,近乎一种宗教的解脱了。如此看来,中国几千年来古典文学历史所传世下来的这四部小说,仿佛是历代人民经过长时间的筛选,把他们作为对自身全面人性的主要历程的系统参照与对于宇宙轮回之大道的根本体现而予以图腾式的信奉的。
相比之下,《金瓶梅》虽然有很高的艺术手腕和对人性某个侧面精到的挖掘,但究竟太偏离了、太浮浪了,它对全面人性的哲理性探讨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这是它难以广泛和公开传播的根本症结。《西游记》虽然是一部非写实的神话小说,吴承恩却在一个“顽猴”身上灌注了何等饱满伟大的英雄的人性,在一个猪猡的躯体之中移植了多少酣畅淋漓的芸芸众生的灵魂。这才是伟大的文学作品所以万古不灭的魅力所在。
吴式南先生对四大古典小说的独特解读让我大开眼界。
人性的呐喊
是人性构成了文学既共时又历时的生命的秘密,如果没有了人的灵性的浇灌,我们简直无法想象人类的文学是由什么酿造而成的。
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娜》描写了一个叫安娜的女人由于厌恶她年老的丈夫而与一个青年军官私奔,抛弃了丈夫和孩子。后来又被军官所抛弃,安娜心灰意冷,就卧轨自杀了。但如果你这样介绍,就大煞风景了。你根本就不能从中感受到安娜的美丽和痛苦,她的爱情的颤动,火热的对幸福的渴望,作为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妇女,不幸的恋人以及真诚的母亲,她最后以死来表示对上流社会虚伪、自私、黑暗的抗议。
否则你就无法理解在苏联卫国战争中,有一个排的红军战士竟喊出:“为了安娜·卡列尼娜,冲啊!”这样鼓动对法西斯拼杀的口号。在这里,一个俄罗斯上层社会的不幸女人竟成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象征,成了人的幸福和美好的象征。在这里,安娜的旗帜变成了一面追求高尚人性的旗帜。
同样,如果说《红楼梦》只不过是写贾宝玉与林黛玉、薛宝钗她们之间的爱情纠葛,后来由于情场失败,一个痛苦而死,一个则做了和尚......,这是对《红楼梦》最残忍的阉割!曹雪芹呕心沥血所创造出的那些天才的篇章,如苏州姑娘的多情和痛苦,孤傲和脆弱,热烈和压抑,薛宝钗的绵里藏针、中庸之道,凤辣姐的笑里藏刀和调包计,以及在热闹的婚礼声中潇湘馆里绝命的叫喊:“宝玉,宝玉,你好......”等等,这些千百年来一直震撼心灵的最强音,是充满了人性的丰富和美丽,庄严和丑恶,痛苦和毁灭,向往和叹息的最具有生命力的声音。
曹雪芹无疑是中国古代最深广最热烈的人道主义者,《红楼梦》就是一面闪耀在中国几千年黑暗王国尽头的最为光辉灿烂、最为五彩缤纷的全面人性的旗帜。
他们都是血泪凝成的诗篇,尼采说他最喜欢读的是那种用“血”写成的书。这“血”,吴式南先生认为就是指人的灵性最为深沉、最为浓烈的浇灌,是人性的呐喊。
人性的符号
卡夫卡的代表作《变形记》描写一个人早晨醒来忽然变成了一只大甲虫(仍具有人的意识),于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最后只得愤愤地、默默地、孤单地死去。故事当然完全是荒诞、超实的。但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现代人的悲剧:生活变化无常,人际之间非常冷漠。强烈地表达了现代人们的压抑感、无常感、危机感。吴先生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和《城堡》、《审判》这三部小说就其对西方现代生活和人民命运的显现,对现代社会人性内涵的揭示来说足以抵得上巴尔扎克九十七部的《人间喜剧》。
海明威的名著《老人与海》是以写实的方法描写的,但它的精神完全是现代型的,小说的自然环境是大海,主人公是一个人类的象征或符号,“老人”与大海的风浪、和鱼类搏斗只是一种隐喻性的情节。它的精神和主旨是表现人类的永恒性的悲剧命运和在大自然(也包括人类自己)的搏斗中永远不失败、永远没有被击倒的英雄气概。海明威希望“人在失败中要仍然不失尊严”,要永远地奋斗和追求。这个象征无疑是现代人类伟大的启示录。“老人”的性格特征虽然缺乏现实主义的细腻和鲜明,但他的所指和内蕴却是异常地巨大。这种象征性寓言性的文学情境构造是现代人类的一大精神符号的创造。
一切文学创造都只是一个文化的符号,一个象征全面人性的符号。蒋和森评论《红楼梦》就是一个伟大的省略号或者伟大的感叹号,外国有评论家说易卜生的剧本是一个伟大的问号。对雨果、托尔斯泰、海明威、卡夫卡等人的作品,也是如此。以这种带着强烈灵气的符号来描述或评价伟大文学作品,才算是传神地表达了这些作品的本质。
所以宋代有个独具慧眼的批评家,竟以一个“气”字,一口评定了历史上六部文学经典的不同特征,他说:“论语气平,孟子气激。屈原气悲,庄子气乐。史记气勇,汉书气怯。”这“平、激、悲、乐、勇、怯”即是作家自身灵气的特征。抓住灵气一点,以一个字就总括了他们各自心灵的底蕴和特色。
豹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有一首题为《豹》的诗:
它的目光被那走不完的铁栏
缠得这般疲倦什么也不能收留。
它好象只有千条铁栏,
千条铁栏后便没有宇宙。
强韧的脚步迈着柔软的步容,
在这极小的圈中旋转,
仿佛力的舞蹈围绕着一个中心,
一个伟大的意志在其中昏眩。
有时眼帘无声地撩起,
于是有一幅图象浸入,
通过四肢紧张的静寂,
在心中化为乌有。
这首诗之所以出色,当然不是因为他就豹写豹,也不是写什么人的力量制服了猛兽,那都是平庸、肤浅的表现。里尔克的慧眼就在于站在人性的追求自由意志这个最庄严的角度来观照巴黎动物园中的“豹”——一个强劲的生命在“千万条铁栏”中被困扼,一个伟大的心灵在单调和乏味之中被折磨,世界的一切“图象”都在“紧张的寂静”中“化为乌有”。
里尔克通过这个动物的悲剧形象,揭示了人和环境的悲剧关系,自由意志和客观世界的深刻冲突。这是一个普遍的全宇宙性的主题。深刻而普遍的人性揭示,使这首诗具有全人类的内容和意义。
从这“豹”,我们会自然联想到人类普遍性的社会命运,会联想到一个个崇高心灵所遭遇到的痛苦,如被缚在高加索山上的普罗米修斯、被压在雷峰塔下的白娘子、被投入牢笼的邹容、遇罗克、张志新、李九莲......以至被终身囚禁的张学良将军,透过铁栏中的“豹”我们仿佛看见了一幕幕人生的悲剧。这一深刻的人性观照,早已超越了动物园里的“豹”,超越了千条铁栏。
豹与人,在里尔克的诗里化为一体,豹有了人性中的悲剧色彩。也只有那些闪烁着人性光芒的诗篇才真正能够打动人心,有着亘久的魅力。
文学的人性观
吴先生说,文学是千面神,是千手观音,她的面目千姿百态,她的色彩万紫千红;而且任何时候,文学总是呈现着全方位开放的形态。这给人们带来无尽的迷恋,无尽的思索,无尽的解答。文学是“人人心中有”,却“人人讲不清”。唯因活在人们的“心”中,文学才显其永恒;也唯因人人都讲“不清”,文学方显其本色。如果能够讲尽了,讲清了,也许就没有文学了。文学永远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向人们做着蒙娜丽莎式的永恒的微笑。“你真美啊,请你停留一下吧”。(浮士德)
那么吴先生心中的文学到底是什么呢?他说这是个愚蠢的问题,回答也是灾难性的回答。
因为文学就是人类自身,文学无法下定义。现代思维的多元方法可以启发我们对文学是什么作出综合的与多侧面的回答,但文学没有标准答案。
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过奢了;说“作品是人生的教科书”太夸张了;说文章(学)是“经国之大业”,把文学太抬举了(廖沫沙有诗“岂有文章倾社稷,从来误国皆佞臣”);说文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是危言耸听。她是人类内心的冲动,痛苦的解脱,苦闷的象征。研究文学只能从她的实际出发,把文学还给她自身,还她以真面目。
从哲学角度看,文学是心与物、人性与生活的二元复合;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内动与外感、表现与再现的二元复合;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文学是人类相互交流情感的代码;
从结构主义角度看来,文学是语音、文字、语词、句子之间的最优性排列系统;
从审美学角度来看,文学是隐喻性和象征性的美听美想的美文创造。
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对特定时代、社会、民族的精神和生活的描摹和折射;
从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展示一定社会、一定人的感觉、情绪、表象、愿望、意向、追求、梦幻等等意识与潜意识的奔腾之流;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对一切奴役与剥削制度的揭露与抗议,是对民主、自由、人权的追求与歌颂,是前进的火光,奋斗的号角;
从接受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是对读者的召唤性结构引发其再创造,并最后到达完善自身的双向过程。
从人类文化学的角度来看,文学是人类进化与心灵发展历程的阶梯式的图腾标志,是实现人、社会、自然三者高度和谐的不倦追求。
我们之所以需要文学、爱好文学、谈论文学,列宁临终前夕还在阅读杰克·伦敦的作品《为了生命》,蒋介石临死时床头还摆着宗教小说《荒漠·甘泉》,可以说文学就是我们人类自身。她与饮食、男女这三者是共同支撑人类生命之三鼎足。饮食是人类生命存在的需要,男女是人类生命延续的需要,而文学是人类生命躁动所折射出来的血与肉的轨迹。它表现为对痛苦的寻求解脱,对邪恶的不断抗争,对爱与美的始终执著,与对希望和理想的不倦追求。文学与人类共同着生命,哪里有人类有生活,哪里就永远有文学。
对人类而言,精神的贫乏难以忍受,生命的躁动高于一切,因此才有了文学,文学就是人性与生命的根本需求。
说文学起源于劳动,太空泛了,这只是一句伟大而正确的空话,正如卡尔·波普尔说:“一个理论传达的经验内容,随它的可否证程度而增加”。文学来源于生活,又不同于生活,是生活与生命的双合力。文学是生活的镜子,是显微镜、望远镜、放大镜、哈哈镜,是一面神奇的魔镜。文学来自人类全面的灵性,文学与人类的灵性共同着生命。人性大于阶级性,阶级性只不过是人性的一部分。文学就是以人类的生活为材料源,以心灵为动力源,心灵在文学中主要体现为人性。表现人性是文学的内核,人性就是人之共同性的生命、心理与伦理要求,它表现为三个层次:一是生理层次上的要求(含生存、男女),二是心理层次上的需求(含认知、意志、想象、爱恨、哀乐、美丑感等),三是理想层次上的需求(含向上、崇高、创造、奋斗等)。人性是在生命土壤和社会土壤上共同生长起来的生命树上所绽放出的花朵。如果说花朵是大自然的艺术,那么人性的文学就是人类社会的花朵。它是无可抑止的,它是文学生命与魅力的根本所在。
人类的感情是普遍、共同的,如爱情、亲情、乡情、童情、旅情,还有孤独之情。感情是人性的河流,是文学的最初秘密。有些文学作品看起来不合理智,不合理性逻辑,却合乎情感的逻辑。一切只要顺应人性,符合人性的要求,因为文学的尺度也就是人性的尺度。她的唯一通行证就是美。
说穿了,文学是人类对自身的全面观照,人类通过文学来求得对自己心灵的发泄、平衡与完善。在某种意义上,她与人类对宗教的信仰类同。不同的是宗教叫人忍受、卑怯、逃遁到虚无的末世,而文学则教人正视人生,抗争罪恶,积极向上。归根结底文学是诉诸人性,是试图作用与改善人的情性(一是娱乐人,二是醒悟人,三是完善或拯救人)。人类从事文学创造和阅读,根本上乃是向着美的王国愉快地挺进。
在文学中,现实主义是本来如此,浪漫主义是应该如此,超实主义是假定如此或感觉如此。文学的中心任务是表现人的全面性情(人性),人性构成了文学最深厚的内容和最长久的魅力。她最根本的作用就是审美。所以有人提出了审美就是人类自由的极至。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就生动地揭示了:人的肉体可以被毁灭,但人的精神永远不可打败。文学是人类最美的奇葩,是一枝永不凋败的花朵,文学不是宣传的工具,也决非金钱的娼妇,文学就是文学。
吴式南先生把他的文论分为本体论、鉴赏论两大部分,他还提出了文学对应论,并用系统论来解读文学语象的生成。他始终把文学看成是心灵的事业,立足于人性,从人的本身出发,找到了文学之所以万古长存的奥秘。这是我对他的文学人性观的理解。
吴式南先生画的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