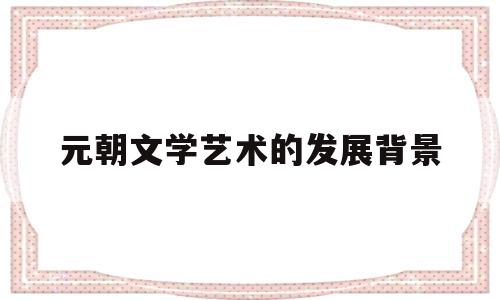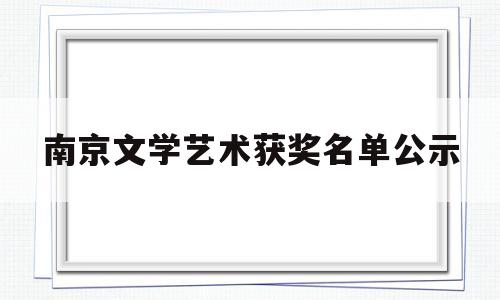文/陈晓萍 公众号/复旦商业知识
本文节选摘自《管理视野》杂志(杂志订阅请至文末获取相关信息)。作者郭玉洁为《生活》、《单向街》主编,Lens 杂志记者,路透中文网、纽约时报中文网、彭博商业周刊专栏作家。
今天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只要出现导火索,一经动员,就成燎原之势。
这种情绪之所以如此容易点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长期以来经由主流的历史叙事,普通中国人的内心已经深植了两种情感:第一,鸦片战争以来饱受侵略的近代史所积累的屈辱;第二,秦汉之后中华帝国的强大与中心位置,使得人们常常瞧不起其他国家,尤其是亚洲的邻国。这两种情绪——屈辱与骄傲——成为了今天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基础。
事实上,关于民族主义的研究和讨论,早已成为热点。民族主义的兴起是全球性的现象,欧洲对难民的排斥、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复兴,只是较为晚近的例子。民族主义可能是有益的,在受压迫时,它要求平等和尊严,但是它同样有可能变得封闭、排外,甚至成为一种压迫和对他人的威胁。
既然民族主义是基于历史的讲述而形成的——比如鸦片战争以来的侵略,比如中国夏商周以来,朝代更替的政治文化连续体——那么,重回历史现场,重新讲述历史,就有可能松动僵化的国族认同,和理所当然的民族情感。
这几年在出版市场上,出现了很多书,就这一现实意识出发,来追问历史。比较有名的有许倬云先生的《何为中国》和李零先生的《我们的中国》。这两位大学者,探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疆域的中国的文化认同、与邻国关系的变化,这种讲述挑战了对于“中国”的主流叙事,也使得我们对于中国传统的认识更加丰富。
《重新讲述蒙元史》,也出自这一文化潮流。本书来自于2014 年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学术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蒙古族的历史学者、人类学者,也有长期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学者,可见虽然谈历史,用意却既深又广。
为什么是蒙元?又为什么称作“蒙元”,而不是元朝,或是蒙古?
在中国的朝代更替中,有两个朝代成为叙事难题,一是元朝,二是清朝。两个来自北方的游牧民族征服了汉人王朝,成为疆域辽阔、武功甚强的大帝国。长期以来,他们被视为异族,虽然是征服者,最终臣服于汉族文化,用儒家思想统治着王朝。
在“中华民族”的概念形成之后,蒙古族、满族不再被视为异族,这两个朝代仍被视为中国王朝的两环,但这种叙述仍然站在汉人的角度,带着心理优越感,并非一种平等的姿态。
在中国之外,关于这两个朝代却有不同的叙事角度。抛开清朝不说,由于在中国北边,存在一个独立的蒙古国,因此关于蒙古的叙事角度尤为丰富。
对于蒙古国来说,蒙古的历史,自然是一个民族的历史,这个民族曾经征服了世界(包括中国),在他们看来,由忽必烈建立的元朝只是当时蒙古帝国的一部分,在元朝之外,还存在其他几个蒙古汗国,远至中亚、欧洲。在元朝灭亡之后,蒙古政权仍以不同形式延续,直到被清朝统治,又于20 世纪初乘大清王朝分崩离析之机,在苏联的帮助下,独立建国。
因此,“蒙元”,名字本身,即容纳了不同的历史叙事。
在中、蒙两国的历史之外,还有一些西方学者和日本学者试图把蒙古史放在亚洲史、世界史之中,进行讲述。在《重新讲述蒙元史》中,学者们不断提到两个名字,一位是日本学者杉山正明,一位是美国学者JackWeatherford(下称他的中文名魏泽福),他们都以蒙古史著述闻名。
魏泽福的两本著作《成吉思汗:近代世界的创造者》和《成吉思汗的女儿们》为我们带来对于蒙古帝国的新认识。在他看来,成吉思汗不是残酷无情的征服者。的确,蒙古铁蹄所到之处,都留下杀戮屠城的故事。但是作者反驳说,从中国到欧洲,文明世界的统治者,残忍并不下于此。况且他认为杀戮的故事,是成吉思汗的战术,令敌人闻风丧胆,实际死伤人数并不如传说中那么多。
在魏泽福的著作中,成吉思汗是一个杰出的军事家。他懂得在不同的阶段联合不同的政治力量,他也是智慧坚强的政治领袖。当他统一了蒙古草原,就将部族古老的习俗编成“大法”,想要结束各个部落之间互相掳掠纷争、永无宁日的历史。
而成吉思汗最重要的历史贡献,魏泽福认为,是他和子孙们打通了欧亚大陆,并拓展、维护商业路线,建立了那个时代的世界体系。货物、农产品、文化、医学、科技,在欧亚大陆流通,中国、印度、欧洲无不因此改变。而获益最大的是欧洲,中国的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就是在那时传入欧洲,如培根所说:“改变了全世界的外观和状态,第一样改变的是文学,第二样是战争,最后一样是航海。”以此为技术基石,欧洲发生了文艺复兴。
魏泽福说:“成吉思汗出身于古老部落,但对于塑造以商业、通信、世俗化大国为基础的近代世界的功劳远胜任何人。”这种站在世界角度对于蒙古历史的新解读,中国台湾“中研院”院士、辽金元史学者萧启庆称之为“令人震撼”。
魏泽福、杉山正明和一些西方学者之所以研究蒙古史,是为了对抗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叙事。他们想证明,在当今的全球化之前,早就有另一种世界秩序,另一种全球化。正如学者吕正惠评论杉山正明著作时所讲:“草原游牧民纵横于欧亚大草原,无意中沟通了东西两方的文明,而其高明的骑射技术比起西方的枪炮和船舰来,不是更具有‘人’的味道,而较少机械性质的遍及生灵的杀戮性吗?”
同样的道理,对于蒙元史的重新叙事,也必将挑战中国以汉人、以中原为中心的传统叙事。在《重新讲述蒙元史》中,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唐晓峰指出,传统中国史有一个基本的地理模式:一个中央大国,加上一个稳定的地理边界带,外面是蛮夷世界。这几乎形成了中国人的世界观。相较而言,由于欧洲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大国历史,中心和边缘常常互相转换,因此形成了欧洲的整体视野。但是,在传统地理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学者(和中国人)常常缺乏亚洲整体历史的眼光,不了解相邻的民族和国家,因此难以解释一些现象,在认识上也有很多盲视。比如北京,唐晓峰举例说,很少人想到,北京原本是王朝边地,是在南北长期复杂、越来越积累的互动历史中,变成了王朝首善,在这一历史地理选择中,北方民族起到关键的、主导性的作用。
这种视角的单一,是这一系列文章都在反思的,尽管所谈的具体问题不一,但是学者们都在强调,要转换视角,“互为主体”,不断透过言说、聆听、观察、学习、实践,往复递进,相互启发,达成“同理心”的认识,从而避免单一僵硬的民族认同和不平等的民族、国际关系。这应该就是重读蒙元史带给我们的启发。
《管理视野》全年4期,年度优惠订阅价258元。长按并识别下方二维码即刻订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