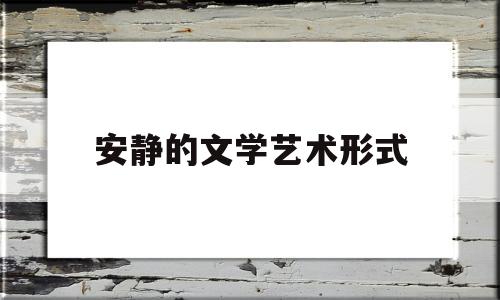心灵深处的人文情怀
对林丰俗山水画的再解读
整理编缉_《当代国画》
文章来源_网络
每每翻阅林丰俗的画作资料或者在展览中看见他的作品时,便觉得有许多想法要说,然而一旦付诸文字却觉得并非易事。这并不是因为作品本身难以解读,恰恰相反,林丰俗的作品所体现出来的明晰与流畅,是艺术界众所周知的。而画家本身为人为艺之风,极为真诚朴实,亦是和他有过接触的人一致的共识。正因如此,用任何华美虚饰的语言来评论他的作品,反而是对画家的不尊重。另一方面,林丰俗的艺术经历,可谓是新中国第一代学院出身的中国画家一个典型的缩影——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求学于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第一届山水专业班,毕业后在地方文化单位供职,并于八十年代初重回美院执教直至退休。虽然林丰俗的艺术经历中没有太多的“传奇”故事可以言说,正如史学家李伟铭所言:“必须承认,林丰俗不属于那类擅长设置‘悬念’的艺术家。换言之,在他的艺术生涯中找不出任何‘惊世骇俗’的故事。”他亦非主动积极参与到各种时代风潮中那一类人,但是他的创作、理念、以及作品中一以贯之的自然情愫与逐步演变的表现手法,却与中国画半个多世纪来所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几次转折息息相关。其中一些作品,更是已经在现当代中国画发展的进程中有了重要的位置。用一句老话来说,林丰俗是一位擅长用“作品”说话的画家。
对于这样一位具有标本意义的艺术家,单纯的就画论画很难读出其深层价值,而将其放在特定的各种情景下来评析他的艺术,则可看出画家与时代之间诸多耐人寻味的关联性。在此笔者试图探讨关于林丰俗的几个问题,这亦都不是什么新问题。例如,作为在“新中国画”历史阶段中架构起其艺术语言的林丰俗,负笈广州美术学院时又得岭南画派山水大家关山月、黎雄才执教,但无论是“新山水画”抑或“岭南画派”都无法将其作品纳入其范畴,这是为何?其次,如何看待林丰俗绘画中不断出现的自然田园因素?而这种“自然 ”,与传统绘画中的“自然”以及建国后写实主义所强调的“自然”又有怎么样的不同?而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艺术重临多元选择之后 ,山水画再次产生深层的震动与嬗变,艺术家风格的顷刻转变已是家常便饭,甚至全盘推翻、重起炉灶的人亦并不鲜见;但林丰俗仍然坚实地沿着自己的信念之路走向更为精深的层面,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于山水画的发展其意义何在?事实上,关于林丰俗的绘画可以衍生出的话题远远不止这些。但对于这些熟悉的问题,我们的考察或许仍未足够。
某种意义上来讲,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当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强力地介入文艺界,新的美术学院教育体系逐步形成并完善之时,中国画创作主旨的统一性与规范性便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致。对于有着诸多法则和文化内涵的山水画来讲,这不能单纯地以绝对的好坏来评判这一影响。但毋容置疑的是,对比起旧式国画教育中隔靴搔痒式的“意会”与不可捉摸的“逸气”,学院式教育在培养艺术家方面更为高效与具有直接性。导师的艺术理念与手法对于学生的影响更是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在林丰俗于1959年至1964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之时,最为重要的两位导师无疑是关山月与黎雄才。岭南画派关注现实、重视写生的传统,在合适的时代语境中被关、黎顺理成章地沿用到了美院的教学当中。黎雄才更是从自身的创作中派生出一整套严谨、系统而有效的教学方法。这从《黎雄才画语录》中便可窥见一斑——黎雄才表现出对具体绘画技巧的极大研究兴趣,并归纳出一套十分细致的、遵循自然规律结合传统笔墨进行创作的方案,从树木出枝用笔乃至山石皴法均有叙述。无独有偶,这些画语录的整理者,正是林丰俗和单剑锋两位山水班的学生。
必须承认,黎氏的教学方法是十分有效的,而且我们不能将其理解为黎雄才的教学理念狭隘——正好相反,在林丰俗及其他同时代受教于黎雄才的画家的回忆中,当时广州美术学院的学风十分开放,关、黎两位先生所提倡的是一种艺术规律,不赞成学生临摹老师自己的创作。但这样一套具体而高效的教学方法,再加上中国画必须“表现生活”的大语境前提,于1956年以《武汉防汛图》获得至高赞誉的黎雄才所采用的具象写实的、折中传统与现代的画风,无疑有着巨大的诱惑力与导向性。黎雄才的山水画产生了诸多直接或间接的追随者,余波直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未停息,甚至一度“黎家山水”几乎成为岭南山水画的代名词。即使在新阶段艺术家们重新面临自由创作的气氛,有意寻求摆脱过往阶段的痕迹,但似曾相识的感觉依旧出现在诸多画家的作品之中。
但之于林丰俗,他在黎雄才身上解读出来的却不仅仅只是笔墨技巧与形式语言。据林丰俗所言,在考入广州美术学院之前,他在家乡已学习过中国画,接受了许良琨、李屏周两位先生的指导。许良琨毕业于上海美专,李屏周则是黄宾虹的学生。海派笔墨与黄宾虹的传统山水理念在这一阶段是否对林丰俗有系统性的影响并不能因此断言,这种启蒙可能更趋向于直观的感性认知。但粤东地区与江浙、海上等地藕断丝连的人文环境,则无疑对于林丰俗审美的形成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潮汕地区遗留了大量的传统农耕社会的社会习俗与道德准则,对于自然的亲近与热爱,植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心中。诸多日常劳作、娱乐、祭祀方式都与地区自然环境紧密结合,并逐渐演变成为岭东的文化特质,直至今日仍组成了粤东人士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感。这种社会结构的特点同样影响到潮籍画家对于中国画的解读与理解当中。西方艺术史学者迈珂·苏利文在其《山川悠远:中国山水画艺术》一书的导言中所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山水画那种自然生动、宁静平和的气氛,在其他文明的艺术中是不多见的。”正因为有着这些先入为主的铺垫,林丰俗在学院苦读时,积极地吸收着各种各样的知识,并在关山月、黎雄才的指导下磨砺出对于传统材质与技法的控制力,建立了严谨的笔墨规范,但却并未完全地投入岭南画派折衷中西、以写生求写实的大纛之下。在回忆起这段求学生涯的时候,林丰俗如此回答:“我们的老师是岭南画派的大师,我们接受他们的教导,接受他们的影响,但是不像旧式的师徒制那样,我们是新型学校。虽然我们具有岭南传统的传承关系,但是我们没有资格去认定宗派。”
在这样的背景下,林丰俗创作于1972年的两张成名作《公社假日》与《石谷新田》显得难能可贵,但也顺理成章。作品中对于视觉空间的营造、前景后景的拉伸推进、树枝的用笔等等不难看出师承的因素,但是这却不是观者观看这两幅画的第一感觉。在有限的主题选择范围内,林丰俗巧妙地把握住了某个侧面去达到“时代主题”的基本要求,而更多的精力则放在了画面轻松悠闲的气氛与视觉效果的营造之上。《公社假日》中热烈的色彩并不是那个时代的固有色,而是为了传达初夏时分怒放的生机以及作者真实的感受。这固然和他的个性有关——战天斗地的题材并非性情温和的林丰俗所喜。但究其深处,则因为在这个阶段,林丰俗已经呈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尽量减少集体意志所施加的单一认识与沉重的“思想内容”,而将绘画母题的重心回归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来。事实证明他所作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两幅画在当时所取得的成就与赞誉,既是画家匠心独运的结果,亦默默昭示着即使在艺术价值极端单一化的时代,人们对于生活中真情流露、平和清新的一面依然有着强烈的神往。而这与中国画内核的某些部分不谋而合。
故此,当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正如三十年前中国画面临表现生活的难题时一样,艺术家们再次面临着选择的困境。只是这次困境的原因是重新面临一个开放的环境,创作的最高宗旨已冰消雪融不复存在,心理上的空白期需要时间来填补。但这对于林丰俗来讲则不是问题。创作于1979年的《大地回春》与1980年的《木棉》在架构上更趋成熟与完整,在画面意境与情感的表达上依旧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且这一次更为真挚,与八十年代初那种“春天”的感觉丝丝入扣。手法上却丝毫没有时代剧烈转变所带来的手足无措与生搬硬套。从此时开始,自然与田园作为一条清晰的主线,开始浮现在林丰俗的山水世界之中,并一直贯穿至今。
关于自然,西方现代美学家苏珊·朗格(S.LANGER)曾经如此描述一个美学上的概念:“你愈是深入地研究艺术品的结构,你就愈加清楚地发现艺术结构与生命结构的相似之处。这里所说的生命结构,包括着从低级生物的生命的结构到人类情感和人类本性这样一些复杂的生命结构(情感和人性正是那些最高级的艺术所传达的意义)。正是由于这两种结构之间的相似性,才使得一幅画、一支歌或一首诗与一件普通的事物区别开来——使它们看上去像是一种生命的形式,而不是用机械的方法制造出来的;使它的表现意义看上去像是直接包含在艺术品之中(这个意义就是我们自己的感性存在,也就是现实存在)”李泽厚在其著作《华夏美学》中引用了苏珊·朗格这一段文字,亦是为对照“天人同构”这一命题对于中国传统文艺创作的影响之巨大。
“自然”与绘画的关系始终是中国山水画所要面对的终极命题。从元代以后的绘画史来看,儒家反功利的价值观,将绘画中不具备写实功能的抽象形式与语言结构关系从这个系统中独立出来,掺入了诸多文哲领域的逻辑关系,并认为这样更能传达更多的文化意义。现实中大自然的形象以及规律不再构成山水画家创作时所依照的“理”与“法”,甚至在发展到清末时已经完全被摒弃。画家们更乐意在纸面上在已定的秩序内探讨排列组合的乐趣,而山水则成为一个承载这些法则的容器,最终走向逐渐衰落和不断重复的局面。而为了反对并打破这一颓势,黎雄才则选择宋画为其绘画血统上的渊源,以自然的形象为其至高范本,并结合写生的方式进行创作,试图唤醒传统山水画中已经消逝几百年的大自然自身的真实气势、以及自然运行的理则,并呼吁人们将侧重点回归于此。但“写生”与“创作”高度统一的手法在“新中国画”发展的盛期取得了令人侧目的成就的同时,也产生了另一方面的影响。正如李伟铭所言:“黎雄才把他所理解的‘写生’与‘创造过程’当成二位一体的看法,或许在逻辑上使‘写生’的价值得到突出强调,但在本质上,却以主体与大自然的对话交融被取消并最终导致主体创造艺术的流失为代价。”黎氏本人的绘画以强烈的笔墨特征与视觉冲击使得这一缺陷处于次要,但在后来者的身上,特别是八十年代之后岭南地区的山水画创作中,却开始有逐渐被放大的迹象。
林丰俗绘画中的“自然”因素,既来自于上述两个方面,又始终与之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对比起传统的文人雅士所空想的理想山水,抑或是加入了诸多现代元素的“现实主义山水”,他的绘画题材都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区别。袁枚《随园诗话》中的名句:“夕阳芳草寻常物, 解用都为绝妙词”既出现在他自己的艺术笔记之中,亦多次被评论家用来点明他题材的特点。“寻常物”在此所具有的涵义,更多的是那些连接起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情境要素。农耕社会数千年来总结出的人和自然世界和谐共存的生活方式,在林丰俗的画面中成为一再吟唱的诗篇。作为亲历过这种生活的一代人,他既有着切实的亲身体会,同时亦细细咀嚼着其中所含的哲理。或许可以这样说,在浓厚的儒家文化中成长的林丰俗,首先是一位耕读修身的儒者,其次才是一位画家。表现自然田园主题对于他来讲,不是居于书斋中的空想,亦并非带有太多的现实目的,而是自然产生的表达需求。“因为中国人认为,绘画的主题与表现形式互不可分,它们共同表达对物质世界无所不包的哲学观念。”苏立文在解释中国山水画的题材决定性之时如是说,这一规律亦在林丰俗身上得以呈现。
梯田、村落、水乡、渡口、耕牛等等景物在他的画面中一再出现,这些似乎都可以归纳进“田园”的母题,但对于“田园”一词的解读方式,在他的绘画中并非一成不变。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初,林丰俗创作的题材很多来自于居住在山区的直接体会,这亦呼应了那一时期中国画的要求。而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开放的艺术气氛、执教于美院的学术环境给予了林丰俗将之前的收获继续深化的外在条件。对于现代风格的山水画创作,他性格中冷静自省的部分则催动其寻求新的表达词汇。林丰俗开始在控制住画面主旨大的方向的同时,尝试更为广泛的表现手法。色彩的运用时而厚重强烈,时而淡雅清透,且愈来愈呈现出各种细致微妙的过渡与渗化效果。线条亦在描绘形象与搭建结构的同时,产生比以往更为明显的韵律节奏的变化。他的灵感来源不拘一格、信手拈来,且张弛有度、游刃有余。譬如敦煌壁画中厚实的色彩关系、汉代画像石中朴拙的造型语言同时出现在《归山深浅去》这样一个具有隐居意味的主题之中,却丝毫没有违和之感。而在《林壑鸣泉》中,自由的线条与斑驳的渴笔互相交错渗透,流动变换的趋势将“鸣”的感觉从画面中提炼而出。正如中国诗歌的优美与精炼,大都与其没有过分的明确性有关,林丰俗对于特定场景的具体描述逐渐退场,画面中的透视感与空间感亦有意被减弱,他更为注重的是那些能调动审美感受的因素,如何以和谐的方式组合于画面之上。而这亦为他的作品带来了毫不重复的视觉效果。
多种艺术语言的控制对于林丰俗来讲并不矛盾,在形式上试图向当代艺术审美探索的行为,以及游历多地写生所得的崭新视觉体验,只会让他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中找寻到自己情感的载体,并衍生出更多的梦中的理想家园。他对“家乡”、“故土”主题的坚持,始终如一——无论是自己的故乡,或者是他者的故乡。而这条主线亦同时处于一种不断推进的状态,进入九十年代以后,他作品中的自然情结再次产生了新的变化——林丰俗绘画中的乡土田园,愈来愈呈现出东方的人文情怀以及理想化的趋势。
事实上,他作品中表达出的价值观——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并非来自于此时他所经历的真实生活状况。在此时,现代中国社会迎来了一个高速城市化的时期。一部分画家放下传统“可居可游”的山水,转向对都市题材的热衷,这亦直接地体现出日新月异的现代生活对艺术界的客观影响。然而,在七十年代便具有某种意义上的“超前”意识的林丰俗,在此时却沉着地依旧坚持着他对大自然的进一步思考。城市生活带来的瞬息万变他并非不关心,但那些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事物,始终不在他的兴趣点上。作为林丰俗多年的挚友,画家林墉曾在文章中打趣地说他:“凡时髦的东西须潮过五年,方敢沾边。”这句话看似在调侃林丰俗的生活态度,其实亦点明了他在艺术创作上的态度。而在近三十年来的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的是,大都市日新月异的生活在维持了高质量的物质生活水平的同时,也带来了无以名状的焦虑情绪与信仰流失。公众怀念过往那种乡间悠闲生活的情绪,在近年来逐渐萌芽并快速增长。而具备这种重要价值的农村,却无时不刻亦无可奈何地面临着被快节奏的现代城市生活所侵蚀的威胁。人造自然景观乃至于新农庄在城市的出现,即是一种补偿性情结的体现。比起千篇一律,熟视无睹的都市水泥森林,清新而遥远的田园气息更能调动观者的情绪波动。于此看来,林丰俗的观念并非落后,而是再一次的走在了时代前端。
《中离溪》这幅产生于九十年代初年代的作品,是林丰俗创作系统中为数不多的大画之一。这幅画较为完整地展示了林丰俗各方面思索的成果。在此时,自然主义的带叙事功能的画法依旧被保留。空间向远方延伸的处理、稳健而坚实的线条、乃至于巨细靡遗的刻画似乎有向过往回归的倾向。但是,林丰俗巧妙地采用了直观的视觉效果,而规避了一览无遗的缺点,在作品中埋下了诸多可供体味的线索。这些线索便是画面中一个个关系上相对完整的情境。老樟树、石亭、木船、水鸭是一处,牌坊、耕牛、稻田又是一处,诸此等等,层层推进又相互交错,如同交响乐般环绕观者,使其产生置身其中的情感交融。而用笔用色的变化亦十分丰富而不突兀,如同溪流涓涓流过,踏歌而行的兴致油然而生。然而这样一个桃源已不复存在,在题跋中,林丰俗以平实无华而略带感怀的文字记述了家乡这一条溪流沿岸景色的变迁。诸多美好的回忆,超越时空,以最理想的状态同时出现在同一场景之中。时间在画面凝固,同时又向各个可能被想象的方向无限延伸,从而产生了隽永的意味。
至此,林丰俗游离于心灵与现实世界之间的艺术探索到达了一个稳定而成熟的状态。“澄怀观化须于静处求之”,黄宾虹的画语之于林丰俗来讲,其“静处”即是自己心灵深处中的人文情结。这种“静”的因素使林丰俗在喧嚣的当下保持着澄净的心境,观察着那些最能触动人心的瞬间,一砖一瓦地构建着心中宁静悠远的家园。而秉承着这样一个稳定的状态,在近年来的作品如《暮春三月》、《飞来禅寺》、《秋壑鸣泉》、《秋水》等作品中,可以看得出的一个新的趋势便是线条的组织愈发密实厚重,用笔则开始呈现出松动而稍带生涩味的感觉。在这种“生涩”中可以读出画家经历一系列的创作冲动,在大的趋势下加入了某些瞬间决定的因素,最后在预想到的效果中又收获了始未料及的惊喜。这种感觉抑或来自于他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伊始未曾间断过的,带有日课性质的写意花鸟画演练。对于笔触感觉的磨砺没有使其变得圆滑,而是使其产生了更多的变化。
林丰俗的创作似乎并未与中国画在近三十年来的各种思潮直接产生关系。但作为一个在八十年代后迎来自己创作的全盛时期的艺术家,林丰俗的价值正在于他如何在各个不同时期坚守自身对于山水的理解,并在贯彻理念的同时展现出一种不断演变与推进的姿态。正如列文森所指出的,“当一种艺术形式的实践者认为它已‘枯竭’时,那它也就真‘枯竭’了。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引伸出相反的结论,因为并非艺术本身真正地发生了‘枯竭’,而是艺术之外的环境改变了人们的主观评价的标准时,艺术形式的实践者才会产生它已‘枯竭’的认识,否则,我们将如何解释某些已认为‘枯竭’了的艺术形式仍然在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具有自己的公众这一现象呢?”在今天,传统山水画与现实主义山水画,同样面临着受众主体与展示空间产生巨变的深层困惑。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场关于中国画何去何从的辩争仍未有结论。中国画如何在文化上的中西关系中找到自身的定位,迄今为止亦是一个无法被解答的老生常谈。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又一个的艺术“大师”走马灯般上台亮相,一个又一个崭新的艺术理念被提上台面,并召开了一场又一场的研讨会。然而旗帜变幻不定的背后,又究竟留下了多少值得被铭记的作品?而在山水画领域,那些乐于在“大山大水”中灌注“沉雄博大”的民族文化精神的“大家”,其作品背后的“宏大”情结,是否有着真情实感作为支撑,亦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可以预见的是,从生活中的真实感情出发,提炼属于东方文化所独有的人文精神内核,依旧是一个不该被放弃的重要过程。在一篇自序中,林丰俗如是说:“我希望于平凡的景物中找到情趣并体悟到诗一般的意境,俯拾即是,触目会心。然而,景随情移,情随时迁,对意境应该不断地有所发现。我不想让成套的笔墨程式或自造程式套住自己的感悟和大自然的盎然生机。”先生谦和的态度背后,是其对艺术规律冷静的认识与恪守。而他所作的选择,则隐藏于那由山泉水所滋润的密林之中,等待后来者的解读。
| 分享朋友圈才是王道 |
整理编缉_夕月慕画
本文/图片 均来自网络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本文言论不代表本平台立场
转载请注明来源
点击“阅读原文” 阅读更多《当代解读》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