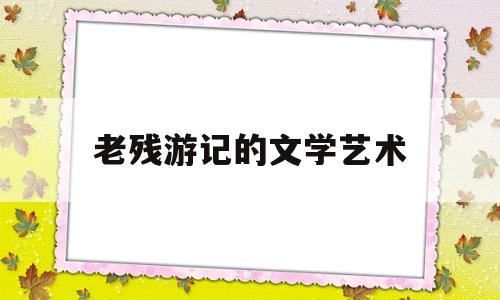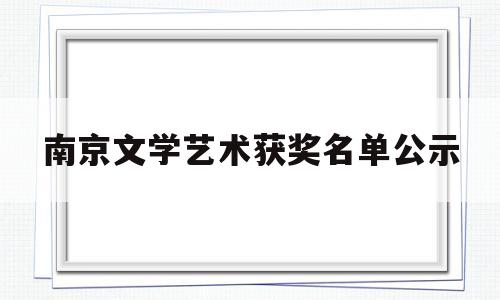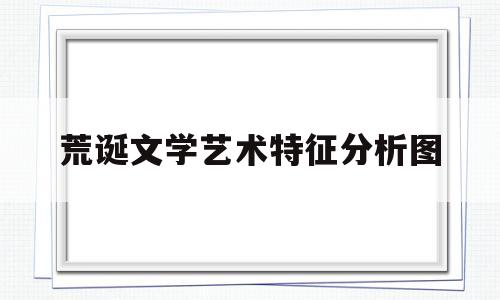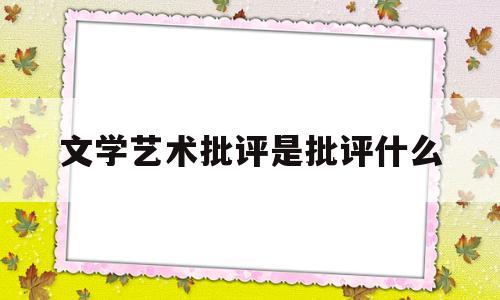几年后,他们搬进了北京国宾馆东侧南沙沟附近,这下与我住的相距就很远了。那时我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走一趟并不容易。更主要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位老人的声望与日俱增,国内外的应酬应接不暇,何况他们对学术都怀着伟大抱负,被耽误了那么多时间,又已进入老境,其心情之紧迫可想而知。我告诫自己尽量少去惊动他们。上世纪80年代我只去看望过他们三次。
在最后一次印象特别深刻:我敲门后,钱先生悄悄把门打开一条缝,一见是我,马上卸掉门链,喊道:“哦,叶廷芳!好久没来了,快进来,快进来。”但当他高高兴兴把我迎进客厅后,他的第一句话却使我颇为意外:“不过,很抱歉,今天只能留你一刻钟,一刻钟!”他看我有些不解,马上从案角上抱起一摞信件说:“你看,这些都是外国来的信件,都等着我回复……”我赶紧说:“我理解,理解,一定遵守约法三章!”钱先生对时间的珍惜,真是锱铢必较,我们这一代人都很难理解了。
后来,读到杨绛先生在《我们仨》中忆及这点,说钱先生在清华读研几年连近在咫尺的颐和园、玉泉山都没有去过。这更使我震惊,因为我自己在北大就读时,每年至少去两三趟。在惜时这点上,杨先生与钱先生也是完全合拍的。“难怪这一对伉俪,不仅学问功底深厚,而且都扎实掌握几门外语。”
在钱、杨那里,对时间的珍惜与对治学的严谨是一致的,决不拿时间换产量。记得在菜园劳动时,我们年轻人曾聊起翻译问题,互相询问一天能译多少字。一般回答都是2000字左右。于是我不无好奇地问杨先生,等着她3000-4000字的回答。想不到她的回答却使大家出乎意料:“我想平均起来每天也不过500字左右吧。”她见大家愣在那里,又补充说:“我翻译其实是很慢的,首先要把每段话的原意弄清楚,然后把每个原文句子统统拆散,再按照我们汉语的语言习惯重新组织句子,把整段话的原意表达出来。”用现在一句流行的话说,她追求“神似”而摒弃“形似”。怪不得读杨绛的译文,遇不到一般译著中经常出现的欧式句子,或是佶屈聱牙的译文。经过语言的提炼,杨绛的译文比一般同类译文的字数要略少一些。
杨绛翻译的这一特长,恐怕多半得益于她早期的戏剧、小说乃至诗歌的创作实践,练就了一手过硬的母语功底。就翻译的风格而论,杨绛的译法几乎跟19世纪欧洲流行的一种译风有关。当时那里人们追求一种内容传神而译文地道,却不拘泥于逐字逐句的真实。鲁迅的裴多菲诗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堪称这类翻译的中国典范,匈牙利原文并非整齐的格律诗。
杨绛的翻译主要是小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审美特点,即都属于巴洛克风格,俗称“流浪汉小说”。她译的法国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西班牙中篇小说 《小癞子》 和西班牙长篇巨著《堂吉诃德》概莫能外。
巴洛克审美风尚盛行于17世纪,主要流行于以意大利、西班牙为代表的中南欧地区。它以一种“怪怪的”艺术风貌与当时在欧洲占统治地位的典雅、庄重的古典主义相对峙,故被主流文学艺术史家们所排斥。直到20世纪它才被人们重新接纳,甚至成为座上客。比如德国的格拉斯因写了“新流浪汉小说”《铁皮鼓》而荣登诺奖宝座。但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的社会主义国家,巴洛克文学艺术依然是个禁区,以致那时我国自己编写的外国文学、艺术、美学史书中,连巴洛克这个术语都很难找到。
实际上,在文艺复兴式微以后,恰恰是巴洛克艺术以巨大的创造活力打破了古典主义仅仅从形式和风格上继承文艺复兴的教条主义僵局,推动了文艺复兴的创造精神在欧洲文学艺术中的继续发展,并诱发了浪漫主义的产生和后来现代主义的兴起。
说起来多么悖谬:仪态典雅、端庄的杨绛先生对那些像模像样的“主义”——扭过头去,唯独接受了这个“不修边幅”的欧洲艺术的“流浪汉”,在周围同行们普遍避讳巴洛克这个禁区时,她毅然闯了进去,一本接一本地翻译了起来,不能不佩服她的艺术慧眼、胆识和勇气!
这使我想起了刚在欧洲文坛崭露头角的歌德,在当时大多数德国人都嚷嚷着要以法国古典主义文学为德国文学发展的榜样时,歌德却斩钉截铁地唱了反调,说:要学就学产生了莎士比亚的英国文学;法国那“讲规则”的古典主义文学“牢狱般可怕”,它“像桎梏一样束缚着我们的想象力”。两位东西方智者可谓心有灵犀。
杨绛先生对巴洛克文学的爱好,不仅反映了她的健康的审美趣味和审美取向,还反映了她的社会正义感,因为按照古典主义的戒律,下等人是不能成为作品主人公的。而流浪汉小说恰恰是所有的主人公都是下等人。他们言行粗俗,举止不雅,常让主子唾骂和嘲弄,但他们也不放过有利时机的狠命一蜇。
杨绛先生在欧洲留学多年,有着过硬的英、法文功底,在她那个年代,英、法语世界有多少重要的文学作品值得她去新译或重译啊!但她偏偏对《堂吉诃德》情有独钟。
是的,这是巴洛克小说的代表作。然而它的原文恰恰是杨绛还没有掌握的西班牙语,而她又不满足于通过其他外语去转译。于是年届半百的她决心迎接这一挑战:再学一门西班牙语。经过二十来年的学与译,她终于攻克了她的翻译生涯的最大堡垒 《堂吉诃德》的西班牙语翻译。为此,西班牙国王亲自为她颁奖。但杨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为使这部扛鼎译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在她“走到人生边上”的时候,有多少重要的工作等着她去“收尾”,她却仍以巨大的毅力将这部70万字的巨著重新校订了一遍。
这又使我想起德意志文化中另一位哲人卡夫卡的箴言:人的心中是不可能没有一颗坚不可摧的内核而存在的。这面镜子又让我们照见了杨绛先生不愧是学界典范的形象。
□叶廷芳(1936年生,诗人,作家、翻译家。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专业。中国德语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环境艺术学会理事。历任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科院外文所中北欧文学室主任。)
来源: 辽宁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