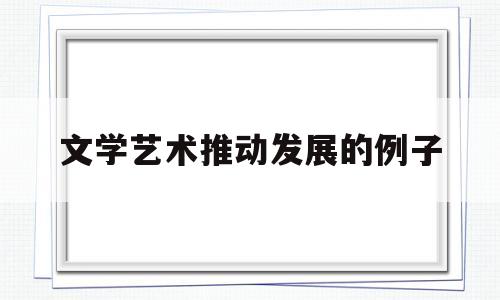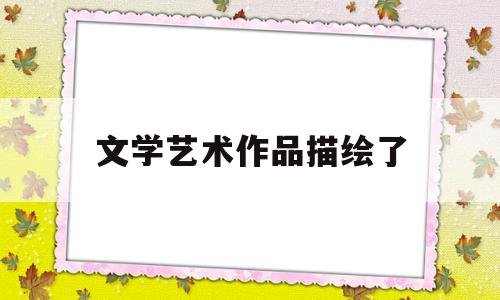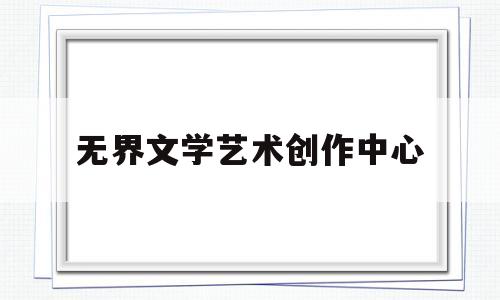虽然,周氏兄弟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都是开山派的人物,但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文风却是迥然而异的,至于后来人生道路的选择,那更是背道而驰。今天,咱们就不谈兄弟情,不谈人生道路选择的背道而驰,单讲兄弟二人的书法。
真正的勇士,
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学生时代对鲁迅先生的印象,
大抵是这样吧——
一位正义凛然的思想家。
在那个时代,
先生的文字就像一把锋利的钢刀,
划破漆黑阴沉的天空……
鲁迅先生作为一位文人学者型书法大家。长期以来,因其在文学上的成就、思想界的地位反而掩盖了他的书法艺术造诣。诞生于20世纪中国大地上的文化巨人鲁迅,其实是书坛上一位“真人不露面”的顶尖书法高手,自有其独特魅力。也许,这是一种遗憾,我们没有将更多的目光放在他的书法成就上。但或许那个时代,先生打心底里想要做的便是一个为新时代而呐喊的人……
郭沫若曾称其书法“远逾宋唐,直攀魏晋。”鲁迅书法多为行书,大幅书作,注重章法、结体工稳、用笔凝重朴拙,舍细节而重大体,气缓意阔、气韵直入魏晋,足见其书法艺术修养之精深。小幅信札、文稿,则信手拈来,心娴手熟,因时变体,草草不工而古法具备,常得天真烂漫之趣,足见其早年书法临池之功厚。
以学养入书,气息高雅自成一格;
以诗情入书,气度沉雄个性鲜明;
以境界入书,气象俊逸翰墨因缘;
以自然入书,气韵生动造就天籁。
鲁迅书法可分早、中、晚三期,各有其特点。
早期为1901年前,书作主要宗法唐宋,上窥二王行书,下掺时人笔意,字体稍偏双逸、秀瓦笔势较放,笔画多见瘦长线条,笔力也愁纱露,结体章法多茂密。此期间笔端时夹少年血气,故韵味稍逊。
中期为1911年至1927年间,书作主要取法魏晋楷行,兼掺章草、篆隶法,书风向朴质、简练、含蓄、疏朗转变。但此期间书作面目较多:如有的存魏晋小楷笔意;有的颜行中兼掺二王法;有的笔画圆浑、书体质朴、章法疏朗;有的融入篆隶笔意、带章草体势;也有的是其前期书风的复出等等。凡此均可视为过渡期书作。
鲁迅《录夏穗卿诗联》 202×45.5cm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与台静农书》
晚期为1927年至1936年间,书法已定型成熟。在鲁迅早年坚厚功底和中期审美选择以及长期劳作、抄录的基础上,出于工用为目的的鲁迅书体从技法到审美已趋成熟和稳定,形成了独自的风格。
鲁迅《书李贺诗轴》 183×56.4cm 1931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鲁迅 《送O.E.君携兰归国》 183×56.4cm 1931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鲁迅 《赠坪井先生答客诮》轴 113.7×32.3cm 1932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鲁迅 《赠郁达夫答客诮》轴 113.7×32.3cm 1932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鲁迅 《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 诗稿 27.2×17.2cm 1932年 上海鲁迅纪念馆藏
鲁迅《行书悼杨铨诗》24.2×27.3cm 1933年 北京鲁迅博物馆藏
在技法上,用笔以中锋圆转、藏而不礴的浑厚线条为主;结体因字成形、形疏意密为特点;章法疏朗雅洁、气缓意逸、洒脱自然为主要风貌。在审美上,以质朴、典雅、自然、古厚为宗旨。
周作人
和鲁迅先生一样,周作人(知堂)也是个一生都只用毛笔书写的近现代文人,无论文稿、书信还是日记,他都弃水笔而不用,而喜欢以兼毫或狼毫的小楷笔,自己磨墨书写。大概除了极少数的文人圈外,并无多少人关注他的字。
有人说,周氏兄弟的思想文章,各不相同,就是书法也绝无相似之处。其实不以为然,虽说从外表看,兄弟俩的书法似乎不太一样,但若从内里分析,他俩却透出一样的闲雅散澹,清逸超凡的书卷气。
尽管有识者或圈内之士认为周作人的书法大有可观之处,但有意思的是,周作人自己曾将他的字大大嘲弄了一番,自贬为“恶札”。他在《知堂回想录》的“北大感旧”中,曾有关于北大著名国学教授刘师培的一段回忆:“申叔写起文章来,真是‘下笔千言’,细注引证,头头是道,没有做不好的文章,可是字写的实在可怕,几乎像小孩子描红相似,而且不讲笔顺……当时北大文科教员里,以恶札而论,申叔要算第一,我就是第二名了。”
周作人致徐耀辰信札
这里的“申叔”,就是在北大以旧学闻名的教授也是“筹安六君子”之一的刘师培。不过周作人在此写刘师培的“字写的实在可怕”,并把自己也拉来垫进“恶札”的第二名,实质是他的文字幽默,玩弄一次小聪明。在贬低人家的同时,也不忘自嘲一下,让受贬的人得到一点心理平衡而已。其实周作人对自己的字还是颇有自信的,否则他就不会常为自己的书封题签,或者经常抄一些诗笺寄赠朋友了。
周作人书法手札
说到诗笺酬唱,有一段故事尚可一说。周作人五十岁时,曾写了两首所谓“自寿诗”,题目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很有意思。后来好友林语堂索诗,他就用八行笺随意抄写寄赠,不料林语堂将手迹影印,发表于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并配上周作人的大幅照片。同期还发表了沈尹默、刘半农、林语堂《和岂明先生五秩自寿诗原韵》。如此一来,果然影响甚大,以致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轰动一时,满城争诵。后来又引来圈内名流的和诗不断,像蔡元培、沈兼士、俞平伯,就连从不写诗的钱玄同也发表了和诗……或许,用现在的话说是“炒作”得太过了,“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鲁迅语),于是又招来了当时一班左翼青年的撰文攻击,遂惹起了一场文字风波。
不过,若就诗论诗来看,周作人的两首“打油诗”写得确实漂亮。
其一云: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请到寒斋吃苦茶。
其二云: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天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致鲍耀明信札
周作人回顾自己五十年人生历程,百感交集,并说“自审近来思想益销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所以,他也就躲进书斋,甘于“消沉”,过着玩玩骨董喝杯苦茶的适意生活。这种状态实际上和周作人的性格颇为吻合,他曾回忆小时侯家中说他“系老僧转世”,所以有“前世出家今在家”之句。而他骨子里所向往的,就是“半儒半释”、不问世事的、悠闲自在的读书生活。体现在他的书法中,就有一点离尘脱俗、好像不食人间烟火者之气。笔墨中虽渗出一种闲雅不群的洒落和自信,但越品越觉出滋味。
周作人小楼深巷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