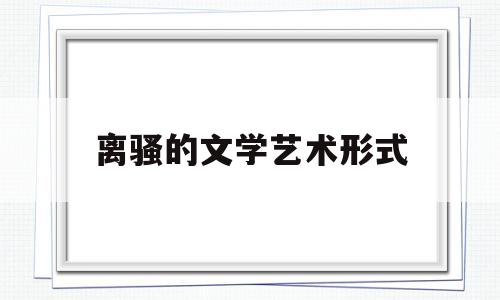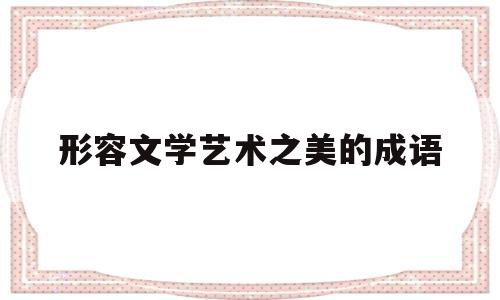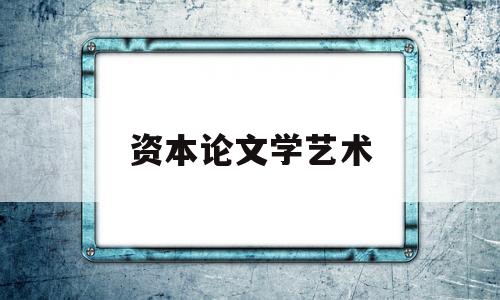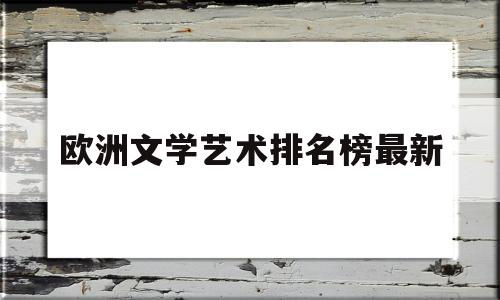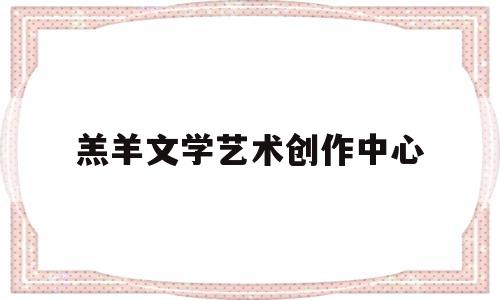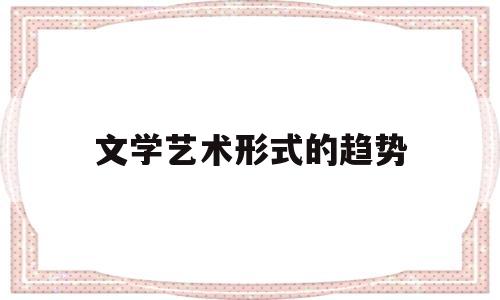屈源——论长诗(节选)
长诗,顾名思义“其言甚长”之诗。它并非为长而长,而是出于对人类生存的普遍境遇和重大精神命题的回应与揭示,才呈现为一派宏伟的语言景观。有些人(如克罗齐、爱伦·坡)认为“长”乃诗歌之敌,连篇累牍会消磨诗歌的效果,所谓长诗是个自相矛盾的说法。对此最有力的反驳来自乔治·桑塔亚那,他在那本关于卢克来修、但丁、歌德及其长诗的小书中写道:“只有飞逝的瞬间、心境、插曲,才能被人销魂蚀骨地感受到,或令人销魂蚀骨地表现出。而生活作为整体,历史、人物和命运都是不适合想像力停留的对象,并与诗歌艺术相排斥吗?我不这么认为。”韦勒克与沃伦则从技术层面指出了长度的重要性:“规模或长度的因素是重要的,但这重要性不是指规模或长度本身,而是指这些因素有可能增加作品的复杂性、紧张性以及宽度。”
长短是相对的概念,《摩诃婆罗多》二十多万行,《伊利亚特》、《神曲》均一万五千余行,《离骚》、《荒原》、《骰子一掷》也就三四百行,但在我们看来它们均属于长诗。既然无法单凭诗句的数量来判定一部作品是否称得上长诗,那么“必须寻找下定义的其他因素”,帕斯这样提醒我们。屈原是中国长诗之祖,从他的作品中,我们无疑能认识到长诗之为长诗的一些关键因素。
▲ 世界文学史上几大代表性长诗
首先在创作方式上长诗便有别于短诗。短诗常常是灵感的产物,所谓“妙手偶得之”,长诗的写作却是一项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工作;短诗似乎可以“无视”传统、游离于传统,长诗却一定根植于传统,乞灵于文学与文化传统。屈原的长诗《九歌》基于楚国的宗教传统;在《离骚》、《天问》中,诗人将他的个人命运自觉纳入了中华文化的历史命运;或许薪传上述传统尚不足以成就一位伟大诗人,屈子之为屈子,更在于他以不世出的天才,创造性地承继和发展了《诗经》传统。时过境迁,对于当代中文诗人来说,传统这一概念更多的时候意味着可选择的多元的过去,而非画地为牢的宿命,各种文化都可以被想像力征用,成为诗歌创作的自由之基。
一首短诗杰作未必非得有“思想”——如果不说它要警惕过分理智化之牵累的话。长诗却一定要“兼有智慧和诗歌语言这两种禀赋”。与哲学著作不同,长诗的思想主要是一种构成性要素,它深深熔炼于作品的肌理,已成为某种象征或神话,正如钱锺书所言:“理之在诗,如水中盐,蜜中花,体匿性存,无痕有味,现相无相,立说无说,所谓冥合圆显者也。”诗歌的思想通常不以辩证或概念的语言方式呈现,其文化精神本质则是一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屈赋精神的核心正在于此。
游国恩曾分析过屈原至少杂有儒、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然而他的作品绝非以上任何一家学说的附庸或演绎。屈原具有“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儒家理念,却异于儒家对圣君的粉饰,他推崇治水的大禹,又直斥其行止有亏,他也敢于把楚顷襄王斥为“壅君”,其“发愤以抒情”的风格也有违儒家中和之道。屈原有道家的出世观念,但他不肯随物推移,宁死也不愿“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他主张改革,反对“背法度而心治”,诗里间有“规矩”、“绳墨”、“方圆”等法家术语,但他绝无法家之刻薄,法家精义端在任法而绝情,这岂是一位“哀民生之多艰”的伟大诗人能够接受的?出生于天文学世家,又曾出使齐国,屈原自然了解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史记》述邹氏之学曰:“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这种史事地理臆测言之,以今观古的方法,也是《离骚》、《天问》的创作手法。不同之处在于,阴阳五行学说中,个体存在被推演至渺小、微茫的境地,大历史乃至宇宙万物都受阴阳五德轮回所左右,概莫能外;而在屈赋中,个人的“内美”与“修能”,深刻地凸显于古往今来、宇宙八荒的背景之下,外在时空之浩渺,被用来表现诗人辽阔深邃的精神世界。屈原以独立的姿态、极端个人化的方式兼容并包,杂有诸家而超越之,这提示了诗歌与某种学说、宗教典籍的区别:诗歌往往“不指向对于天地宇宙的终极的正确解释,它更关心揭示人类自相矛盾的、浑浊的、尴尬的生存状态”,为此它更强调拓展而非净化、一致,更希望将离心的事物纳入更大的统一体,而非消除它们。长诗常常包涵许多(可能互相抵牾的)知识,拿《天问》来说,它涉及了天文、地理、神话、历史、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的庞杂知识,然而这部长诗“既未专注于某一门知识,又未使其偶像化;它赋予知识以间接的地位,而这种间接性正是文学珍贵性之所在”。与此同时《天问》向我们展示了一种伟大的怀疑主义精神。屈原拒绝不加审视地接受权威习俗、史料典籍、自然法则、社会规律提供的解释,他力图通过自我不懈的追问寻找存在的真实依据。《天问》通篇一百七十余问,包罗万象的问题最终汇为一个问题——天人合一的存在问题。海德格尔认为,存在问题就是要从存在者身上逼问出它的存在来。他指出应以发问的存在者为出发点,让存在开展开来;而解答存在问题等于:“就某种存在者——即发问的存在者——的存在,使这种存在者透彻可见。”《天问》看似从“遂古之初”(宇宙的起点)写起,其实篇首的“曰”(隐身的发问者)才是真正的出发点。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伟大的无人称写作,在存在之天命的遣送中,任何意识到自己孤悬于茫茫宇宙的个体,都可以自行代入。《天问》这种惊世骇俗的百问而无一答的方式或许在暗示我们,存在的惟一真实依据就是追问本身。而“曰”字也让我们领悟到,诗性智慧本质上是一种启示,就像这“一字之师”,迄今仍然玄奥地阐发着语言和存在的关系。
▲ 伟大诗人屈原
屈原提示我们,杰出的长诗不仅深闳地探索了人类的经验世界与想像世界,往往也进一步开拓了语言世界。屈原无疑是一位语言大师。他变四言为长句,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诗经》的比兴手法一般比较简单,多是触景生情的实写,而屈赋的比兴复杂瑰奇,多虚构想像之辞);屈赋还大量运用连绵词、叠字,以增强诗歌的音乐效果;《诗经》中尚不普遍的语气词“兮”在屈赋中也获得了最广泛的使用,它在诗句中的位置、功能更加灵活多变;楚地方言的运用更是屈赋一大特色。而屈原对当代中文诗人更深刻的启示在于:他并没有用一种(也许从来就不存在的)“纯正汉语”进行写作。据岑仲勉考证,屈赋中的“离骚”、“荃”、“灵”、“羌”、“些”等二十余字词皆来自古突厥语,而“飞廉”据最近研究证实来自东夷语,这些词语可以说是古汉语的异质成分,不属于商周语言体系。据说诗歌要“纯洁部落的语言”,于是某些人抵触来自日本的汉字词,而那些汉字词有些是被赋予了现代涵义的古汉语词汇,有些是根据汉字的语素意义和构词法构造出的,似乎不应算外来词,相反,它们恰是对汉语自我更新能力的一种确认;对于真正的外来词(音译词),其实也不应抵触,“离骚”、“飞廉”入诗就是最好的例证。跟“语言的民族主义者”相反,某些“语言的现代主义者”并不拒绝外来词,却极力反对文言语汇;而“口语派”诗人又偏狭地独尊口语。殊不知两千年前屈原已然揭示了一个诗歌语言的普遍真理:方言外来词、口语书面语、古语今言、成语自造词,皆可为我所用,端看用得是否诗意盎然。
帕斯说:“在短诗中,开头和结尾几乎融为一体,几乎没有发展……为了维护一致性而牺牲了变化,在长诗中,变化获得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又不破坏整体性。”他还指出长诗复杂的发展是一个破格与复归的过程。复归是一项基本准则:格律、主题意象、主导动机、固定程式、重复句式或重复语,都是强调整体性、连续性的符号或标志。相反的运动是“断裂、变化、创新,总之是意外之举:破格的范畴”。帕斯总结道:“我们称之为发展的东西无非就是惊奇与复归、创新与重复、断裂与持续的结合。”而《九歌》就是一个破格与复归完美统一的典范。复归的轴心是结构,《九歌》的结构可以直观地排列为: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礼魂》
《九歌》所祀之神完整地包括了天神、地祇、人鬼三类。天神有诸神之长东皇太一,有代表自然力量的东君(日神)、云中君(云神),和经办人类命运的大司命(死神)、少司命(送子娘娘);地祇有楚地方神湘君湘夫人及河神、山神;人鬼为《国殇》中的阵亡将士;《礼魂》是作为整部作品尾声的送神终曲。意味深长的是,地祇湘君湘夫人竟排在天神大司命少司命之前,这很可能是因为楚人极为尊崇湘君湘夫人这两位本地守护神,有意抬高了他们的地位,为此屈原不吝篇幅予以重点书写;另一方面,大司命少司命经办人类命运,故近于人鬼,但他们又要位于另两位地祇河伯山鬼之上。《九歌》以主天神东皇太一和人鬼为轴,其余八位神祇对称排列,一侧神祇为“阳”,另一侧为“阴”。除了这种中轴对称的结构美学,《九歌》更是以“灵”作为统一众神、串联整部作品的关键词:
《东皇太一》:“灵偃蹇兮姣服”;
《东君》:“思灵保兮贤姱”、“灵之来兮蔽日”;
《云中君》:“灵连蜷兮既留”、“灵皇皇兮既降”;
《湘君》:“横大江兮扬灵”;
《湘夫人》:“灵之来兮如云”;
《大司命》:“灵衣兮被被”;
《河伯》:“灵何为兮水中”;
《山鬼》:“留灵修兮憺忘归”;
《国殇》:“天时坠兮威灵怒”、“身既死兮神以灵”。
需要指出的是,《大司命》中“灵衣兮被被”是形容大司命服饰的,《少司命》一诗虽无灵字,可诗中那句“荷衣兮蕙带”同样是描写大司命所穿“灵衣”的,所以《少司命》道是无灵却有灵!真正无灵的是《礼魂》,因为曲终灵散。如此匠心,怎一个灵字了得。
▲ 屈原《九歌》
《九歌》抒情风格之变化从庄雅的《东皇太一》开始,经豪放《东君》、婉约《云中君》,抵达高潮二《湘》,再返回风格分别类似《东君》、《云中君》的《大司命》、《少司命》(《大司命》豪放里透着威严,《少司命》婉约中充满惆怅,两者的关系也比较晦涩纠结,不像《东君》《云中君》那样一清二白。这是因为大司命与少司命象征了死亡与生命之间的关系,诗中我们能感觉到后者对前者的敬畏、怨怼……),再到如“日”朗照的《河伯》之爱以及如“云”变幻的《山鬼》之情,最后是悲慨的《国殇》与悠悠《礼魂》。这只是一个非常粗线条的勾勒,《九歌》的发展变化远比任何概括都要复杂微妙。就拿地祇四神来说,同是爱情题材,《湘君》、《湘夫人》是内心独白,《河伯》更着眼于外部事件,《山鬼》则内忧外“幻”;或者说,《湘君》、《湘夫人》整体是一出戏剧,“二湘”的独白也是某种对话,《河伯》是一首叙事诗,描写了河伯与恋人从相会、游河到送别于南浦的完整过程,而《山鬼》是一首如梦似幻的抒情诗。在情节上,湘君与湘夫人处于赴约途中还未见面,河伯与恋人不仅见面了还一起游玩,而山鬼来晚了,其男友失约了;“二湘”是夫妇之爱,《河伯》描写了成熟男女的恋情,山鬼乃初坠情网的少女。在情绪基调上,“二湘”焦急、深情且幽怨,河伯比较轻松快乐,亦有淡淡哀愁,山鬼的心思却患得患失、变幻莫测。这些由“阴阳”发动的变化,令人叹为观止。
《九歌》不仅是符合特定仪轨要求的大型乐神仪式诗,亦是屈原用后世叶芝、庞德所谓的面具手法撰写的一部长诗,屈原的思想情操、个性旨趣在众神的面具下微妙流露,呼应着他的其他作品。《九歌》充分说明长诗是一种综合创造,是“在均衡合度和关联意义上对复杂的综合体的把握”。在屈原笔下,抒情、叙事、写景、哲思、戏剧性、组诗性、音乐性,各显其能又融会贯通;神话、现实,交相辉映;细部摇曳多姿,整体多变而统一,其各层次的审美价值质互相配合,形成了一种复调和声的效果。
基于长诗的上述特点,它最终在阅读中呈现为一种具有多价值性的“难美”。已故诗人骆一禾将长诗和写作长诗的诗人看成是一个“博大生命”的现象,这生命不是“苍生一芥”,而是“深层构造的统摄和大全”。屈原即是如此,我们民族的这位源头性诗人令后世读者高山仰止又望洋兴叹,真正进入他的一系列长诗远比进入杜甫的世界、李白的世界困难得多,但你又没办法将他绕过去。骆一禾在《光明》中这样写道:
长诗于人间并不亲切,却是
精神所有,命运所占据
屈原作为中国长诗传统的源头与核心,依然是一个给予我们无限启示的,涌动的意义之源,其巨大的身影深深笼罩着当代中文长诗。就形式而言,当代的长诗写作不是《离骚》般鱼贯而下的长诗,就是《九歌》那样的组诗型长诗,并未突破屈原开创的长诗模式。就内容而言,《离骚》的自我虚构,《天问》的宇宙之问,《九歌》的人神世界,《招魂》的幽冥之旅,《哀郢》的现实哀歌,《橘颂》的托物言志,《涉江》的流亡之诗,《惜往日》的自挽之诗……每一首都是垂范后世的某种诗歌类型的伟大典范。所谓屈原,就是一个博大渊深、精美绝伦的诗歌宇宙,就是创造力本身。现代西方诗人,几乎已没有谁像荷马那样写诗了,而他们的写作却也有意无意地接近了屈原。
一首长诗总是饱含忧患意识。也许一首抒情短诗可以为片刻的闲适、欢愉而作,为风花雪月而作,长诗却无疑是沉重的危机写作。它或许不出自经验的强度,却一定基于经验的深度与广度;它或许没有激情之魅,却一定意味着智慧之能——而“长”在甲骨文中正是象形一个拄着拐杖的老者的侧影;最重要的,长诗虽为个人的创造,却“不停留于个人的”,总是力图“回应共同的需要”。
长除了与短相对,还有辽阔之义(如“秋水共长天一色”)、高大之义(《吕氏春秋·谕大》:“新林之无长木也”)、久远之义(《说文》:“长,久远也 ”)。长诗之长兼有以上诸义,一首杰出的长诗总是深深地蕴涵着当下世界,又不断回溯过去,直至本源;它也许不提供救赎真理,但它创造价值,拓展我们的意识,熔炼我们的心魂,并力图对人类的未来有所启示。在这个意义上,长诗可谓是人类文明本身的一个隐喻,就像屈原《九歌》的结尾所写的那样:
春兰兮秋菊
长无绝兮终古
“
作者简介:秦晓宇,诗人,文学评论家,纪录片导演。著有《虚度》、《夜饮》、《长调》等诗文集,新诗札记《七零诗话》,及诗论专著《玉梯——当代中文诗叙论》。编有《马雁散文集》、《新的一天》(许立志诗集)、《我的诗篇——当代工人诗典》,《铁月亮——中国农民工诗选》(美国白松出版社),并与诗人杨炼、英国诗人W.N.Herbert共同主编当代中文诗选本Jade Ladder(英国血斧出版社)。2007年获刘丽安诗歌奖, 2013年应邀参加第44届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2015年起任足荣村方言电影节评委会主席。执导并担任总撰稿的纪录电影《我的诗篇》获第18届上海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2015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年度最佳纪录长片金红棉奖。另执导纪录片《方言电影》、《炸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