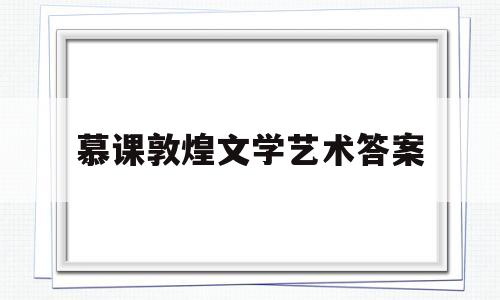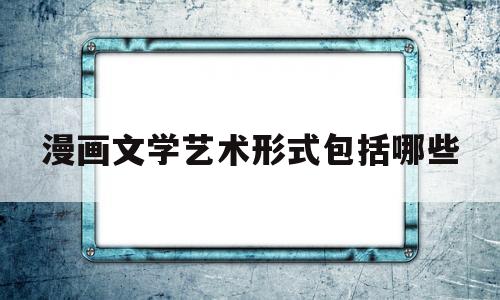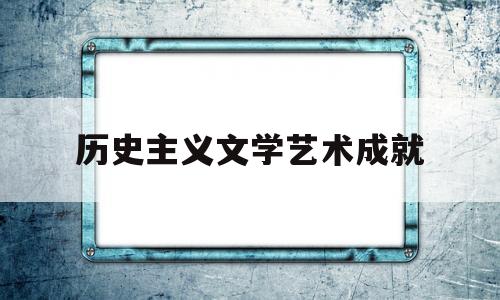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所谓人文精神,是与科学精神相对而言的,从根本上说,是指人生信念、社会理想、生存方式等方面的价值追求。与西方源起于古希腊时代的以主客对立、渴望征服自然为主导的文化视野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更为丰富地蕴含着关于人的自我修养、人类社会本身的秩序建设、人与自然的关系之类人文精神。正是这些方面的人文价值追求,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诗人、作家的心灵,形成了中国古典文学鲜明的精神个性。
(一) 刚正不屈的人格追求
恪守正义,坚持真理,刚正不屈,崇尚气节,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看重的人格风范。孔子所赞叹的“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曾标举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等,推崇的正是这样一种人格特征。据《左传· 襄公二十五年》载,齐国大臣崔杼,杀死庄公,“大史书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这几位较早见之于史册的齐国文人,即可谓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楷模,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不畏强暴、刚烈不屈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赞赏,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旺盛的脉绪。在不同时代,大义凛然如齐史官那样的诗人、作家,纷涌迭现,不可胜数。遭到佞臣陷害而被放逐的屈原,不顾个人得失,仍在《离骚》中昂然宣称:“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愿依彭咸之遗则。”司马迁尽管因为李陵辩护而受宫刑,但仍刚正不阿,在出狱后写作的《史记》中,仍秉笔直书当朝开国皇帝刘邦的无赖言行与奸诈性格,对于同时代的汉武帝的奢侈浪费、迷信方士之类,也给予了大胆的讽刺与批判。不肯与黑暗官场同流合污的晋代诗人陶渊明,勇敢挑战世俗,决然归隐,在晚年陷入“偃卧瘠馁”之境时,仍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柳宗元因积极参与当时撤办贪官污吏之类的政治改革而遭到迫害,贬逐永州之后,亦仍固守高洁,“独钓寒江”。此外,在面对强暴、愤然不屈的窦娥(关汉卿《窦娥冤》),在大义凛然的李香君(孔尚任《桃花扇》),在敢于反叛天庭的孙悟空(吴承恩《西游记》)等这样一些文学形象身上,闪射出的也是有着铮铮铁骨的中国古代作家的人格光辉。
在国难当头、外敌入侵的历史背景下,这种人格精神又常常化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过零丁洋》)、“壮士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陆游《书愤》)、“今生已矣,来世为期。万岁千秋,不销义魄。九天八表,永厉英魂”(夏完淳《土室馀论》)这样一种精忠为国、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这里特别值得提及的是,本以婉约风格著称的女词人李清照,也曾写下过“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乌江》)的雄健之作。
文学,是一种最富于个性气质与独立人格追求的精神创造活动,只有缘此产生的诗文,才能见出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推重的“风骨”,才能“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虽亦不乏奉帝王之命而为之的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甚至阿谀奉迎的“应制”之作,如明初诗坛上出现的杨士奇、杨荣等人为代表的台阁诗等,但毕竟为人所不齿,不能代表中国古典文学的主流方向。而真正代表中国文学的伟大成就,时常回荡在历代读者心头的正是那些充分张扬刚正不屈的人格精神之作。
(二) 救世济时的道德信念
中国古代文人向以济时救世、安顿天下为己任,有着强烈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意识,向往着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自由平等的人间乐园。孟子所设想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宋人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所称颂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杜甫所希冀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道德情怀。
正是出于匡正天下的使命意识,经世致用、文以载道成为中国古代文学创作的主导追求。早在汉代,桓谭就已在《新论》中提出了对“美而无采”的“丽文”的批判;唐代的陈子昂、李白等人亦曾标举“风雅”,痛恨六朝以来的浮艳诗风,白居易则明确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从创作实践来看,中国诗人、作家常以嫉恶如仇的犀利笔触,抗拒着社会的不公,抨击着现实的黑暗,倾诉着民间的疾苦。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已多见这类惊心动魄之作。如《伐檀》《硕鼠》《鸨羽》《黄鸟》等诗篇,尖锐地讥讽了疯狂掠夺的贵族,愤怒地控诉了奴隶社会的残酷与野蛮,发出了“悠悠苍天! 曷其有所”的厉声斥问。在此后不同的历史时期,如控诉战乱、悲悯生灵的作品,如王粲的《七哀诗》,杜甫的“三吏”、“三别”、《北征》,张养浩的著名散曲《潼关怀古》等,揭露统治者骄淫奢侈、横征暴敛的作品,如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白居易的《卖炭翁》、关汉卿的《窦娥冤》及蒲松龄的《促织》、《席方平》等,层出不穷,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震撼人心的一大序列。
正是出于对人间乐园的向往,中国古代的诗人、作家,或以豪迈的气势、赤诚的胸襟,写下了大量诸如“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杜甫《洗兵马》)、“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龚自珍《己亥杂诗》)之类渴望战乱永弭、呼唤人间太平、向往自由平等的诗篇;或以浪漫主义的艺术手法,虚构出一个“土地平旷,屋舍俨然”“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男女老少怡然自乐的“桃花源”世界(陶渊明《桃花源记》);或想象出一个人们相互谦让、连官场权贵亦和蔼可亲、清廉俭朴的“君子”之国(李汝珍《镜花缘》);或以粗犷的笔墨塑造了武松、李逵、鲁智深(施耐庵《水浒传》)、黄天霸(《施公案》)、十三妹(文康《儿女英雄传》)、白玉堂、蒋平(《三侠五义》)等众多“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解困济危,舍己为人”的英雄好汉、侠客义士的形象。
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
(三) 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在中国古代诗人、作家笔下,虽不乏由于世事渺茫、生活困顿或仕途失意而生出的人生无常的悲叹和梦幻破灭的哀怨之类,但构成文学史主调的则是高亢激越、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渴望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曹操那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龟虽寿》),千百年来,一直鼓舞着许多人的心灵。陈子昂的“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感遇诗》)、王维的“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老将行》)、陆游的“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诗句,至今读来,仍令人振奋不已。尤其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笔下,那些“抚剑夜长啸,雄心日千里”(《赠何七判官昌浩》)、“气岸遥领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流夜郎赠辛判官》)的狂放诗句,更是以其英姿逼人之状,激人奋发。这位杰出的浪漫主义诗人,直至逝世前,在其绝笔之作《临终歌》中,仍以大鹏自况,字里行间喷涌出来的仍是渴望“飞振兮八裔”“风流兮万世”这样一种豪气与雄风。
二是坚不可摧的英雄气概。从“精卫填海”“大禹治水”之类的神话故事中即可见中华民族早在创生之初就已形成的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后世的许多作品,亦常是缘于这样一种精神而为人推赏。“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关汉卿的这一名曲《不伏老》,便正是缘于其中汹涌的刚烈决绝之气,而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亮点。在司马迁笔下,那位兵败垓下的项羽,之所以千古为人传颂,亦正在于其虽然身陷绝境而决不气馁,毅然率部下“下马步行,持短兵接战”,一直战斗到最后一刻的英雄本色。另如《水浒传》《西游记》《三侠五义》等小说作品,之所以深为中国人所喜爱,重要原因也在于作家生动地刻画了一系列敢作敢为、大呼猛进的英雄豪杰形象。
三是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无论面对社会危局、时代忧患,还是人生挫折,中国诗人、作家常常表现出一种积极乐观的情绪。“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登池上楼》)在久卧病床,且仕途失意的东晋诗人谢灵运笔下,仍透露出这样一种欣欣向荣的春之气息。唐代诗人刘禹锡在被贬官23 年之后,仍如此豪迈地写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深谙多灾多难之中国历史的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戊戌政变失败之后亡命日本时,犹写下了《少年中国说》这样一篇充满乐观主义激情的政论散文。文中写道:“天载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 壮哉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 ”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感人肺腑。
中国古典文学,正因这样一种不屈不挠的奋进精神,增强了刚劲的风骨与神韵;也正是这样一种自强不息的豪情,构成了中华民族不息的生机与活力。
(四) 自由率真的生命向往
在中国古代文学理念中,虽然一直十分重视厚人伦、美教化、文以载道之类功利目的,但与此同时,在文学史的长河中,反抗不合理的封建礼教束缚的呼声,也时成声势;鄙弃世俗名利,傲视权贵,自由放达,率真任性,敢爱敢恨的生命追求,亦震撼千古。中国最早的诗论典籍《毛诗序》就已指出,诗歌创作的特征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唐代诗人韩愈强调“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明代思想家李贽亦强调好文章乃出自“绝假纯真”之“童心”(《童心说》),故应顺性而为。另一位明代学者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得更为明确:“人心有一部真文章,都被残编断简封锢了;有一部真鼓吹,都被妖歌艳舞湮没了。学者须扫除万物,直觅本来,才有个真受用。”这些文论主张体现出来的正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更富于现代人性精神的生命渴望。
从具体文学作品来看,在诸如“被褐出闾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左思《咏史》其五)、“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两岸舟船各背驰,波痕交涉已难为。只余鸥鹭无拘管,北去南来自在飞”(杨万里《初入淮河》)之类诗作中,涌动着的亦正是这样一种渴望自由之情。在蒲松龄笔下那个直言快语、敢笑敢闹、“狂而不损其媚”的婴宁;《红楼梦》中厌读“四书五经”、藐视功名利禄的贾宝玉、林黛玉;《儒林外史》中笑傲王侯、不慕荣华,向往“天不收,地不管”之生活境界的杜少卿、王冕;《水浒传》中言行无羁、富有反抗精神的鲁智深、李逵等人物形象身上,也无一不体现了中国古代作家内在心性的自由放达。
这样一种生命追求,尤其见之于许多大胆追求纯真爱情的作品中。如《诗经》中的《关雎》《将仲子》,唐诗中李商隐的《无题》,宋词中李清照的《醉花阴· 薄雾浓云愁永昼》、陆游的《钗头凤· 红酥手》,元杂剧中的《拜月亭》《西厢记》,及明清文坛上出现的汤显祖的《牡丹亭》、洪昇的《长生殿》等等,亦正是缘其率真赤诚的人性追求,打动了历代无数读者的心灵。
(五) 汇通天地的宇宙情怀
当今世界,由于人类自身物欲的无限膨胀,对生活资源的竞相掠夺,人类实际上也已为自己制造了以及正在制造着许多令人怵目惊心的灾难:森林面积与物种数量正在锐减,空气与水源严重污染,生态环境在日趋恶化。我们赖以生存的“宇宙岛”“地球村”已经惨不忍睹,岌岌可危。因此,早在20 世纪初,就有不少西方学者将目光投向了对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关注,提出了“生态伦理主义”之类主张,强调人应与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和平共处。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方面,我国的许多古圣先贤早已有着清醒的认识,体现出一种注重人与自然和谐并存的宇宙情怀。《易传· 文言》中已有“与天地合其德”之说,老子的《道德经》中已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著名论断。另如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荀子的“谨其时禁”以及宋人张载明确提出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西铭》)等哲学命题与人生主张,分明就已包含着弥足珍贵的现代西方学者所倡导的“生态伦理主义”思想。
与之相关,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另一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早在南朝宋代,随着谢灵运、谢朓等著名山水诗人的出现,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就已引人注目地进入了中国人的审美视野,正如朱光潜先生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指出的,中国人在公元5 世纪前后的晋宋之交就兴起了自然情趣,而西方人则在公元18 世纪左右的浪漫运动初期才兴起,要晚于中国人1300多年。此后,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诗文中歌颂自然、田园风光、花鸟虫鱼之类自然美的作品一直异常发达。在诸如“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王勃《滕王阁序》)、“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王维《鸟鸣涧》)、“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李白《独坐敬亭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杜甫《水槛遣心》)、“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东坡《饮湖上初晴后雨》)的佳句中,在柳宗元的“永州八记”、张岱的《湖心亭看雪》等散文名篇以及《西游记》《水浒传》《红楼梦》等小说中的景物描写中,均可见中国诗人、作家对自然美的钟情,以及“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样一种关爱万物、主客化一、汇通天地的宇宙胸襟。在目前人类的生态伦理意识正在觉醒勃兴之时,中国古典文学中蕴含的这样一种宇宙精神,无疑是值得大加发掘、弘扬光大的。
当然,我们也要意识到,以现代文化眼光来看,由于文化血缘、社会体制、生态环境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在我国古代文学所流露的文化观念中,也存在着某些方面的局限与需要分析批判的糟粕,如“官本位”意识、“奴性”意识、“杀伐”之气等。这些局限与糟粕,也在多方面束缚了中国诗人、作家的手脚,压抑了其创造活力,影响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需要认真地加以甄别与扬弃。
选自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传统文化读本》
阅读链接:
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传统文化读本》
(统筹:启正;编辑: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