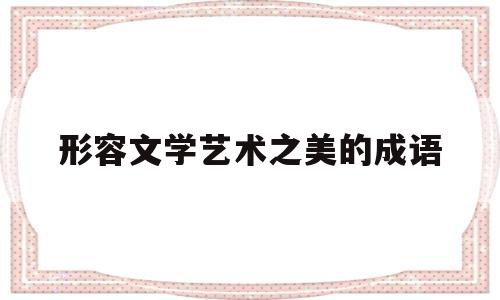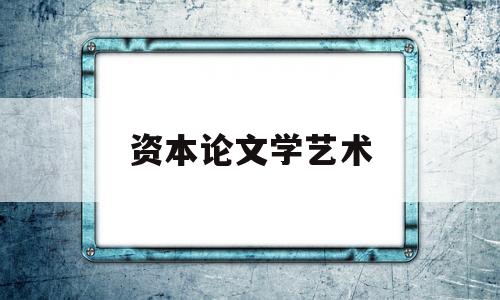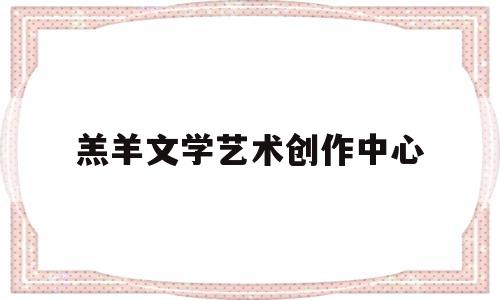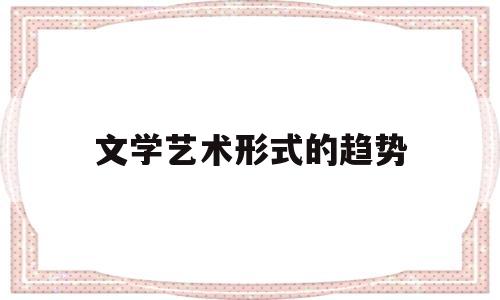国学智慧
「最受欢迎的传统文化及热门公号 强烈推荐 」
国学智慧 | 阅读经典 | 悟道| 情绪控制 | 创业哲学| 婚姻幸福
总编辑:胡可如
各位仁兄大家好 这是一篇讲述宋朝繁华史的好文章,喜欢历史的朋友们可以阅读哦
一
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是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对宋代却不吝于赞美,评价非常之高。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宋代武功远不及汉唐之盛,却何以大获海外汉学家的青睐呢?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及情感的取舍。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以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许多海外汉学家在论及中国宋代的时候,似乎还特别喜欢使用“革命”之说。比如英国汉学家伊懋可认为,唐宋之际发生了一场“经济革命”,包括农业革命、水运革命、货币和信贷革命、市场结构与都市化的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日本学者斯波义信也提出“宋代经济革命”说,并列举了宋朝的农业革命、交通革命、商业革命以及都市化方面的重大变迁;《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也说,“宋朝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对整个欧亚大陆有重大的意义。”美国学者郝若贝则认为宋代中国出现了“煤铁革命”。仿佛不用“革命”一词,不足以强调宋代文明与之前时代的深刻差异。
大概正因为看到了唐宋之际发生的种种“革命性”变迁,又有许多汉学家相信,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
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率先提出“唐宋变革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
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
另一名日本学者摅薮内清也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
法国汉学家谢和耐说道:“十三世纪的中国,其现代化的程度是令人吃惊的:它独特的货币经济、纸钞、流通票据,高度发展的茶、盐企业,对外贸易的重要(丝绸、瓷器),各地出产的专业化等等。国家掌握了许多货物的买卖,经由专卖制度和间接税,获得了国库的主要收入。在人民日常生活方面,艺术、娱乐、制度、工艺技术各方面,中国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国家,其自豪足以认为世界其他各地皆为化外之邦。”
另一位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中国知识圈很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
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11、12 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
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称:“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则说道:“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
总而言之,在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显然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
二
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
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
商业化。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
市场化。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
货币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
城市化。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
工业化。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
契约化。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
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
平民化。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
平等化。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
功利化。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
福利化。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
扩张化。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
集权化。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制。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这里的“专制”一词如果换成“王权制”,会更准确。
文官化(理性化)。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
法治化。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
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到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
三
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华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
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
——“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
——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赋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
——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贸易总额超过2000万贯。
——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
——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
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
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
为什么宋人必须大量铸造货币?因为需要满足货币化的时代需求。不独市场交易以货币结算(在自然经济时代,还可以以物易物);官吏与雇工的酬劳,也要用货币支付,而在宋代之前,工资以实物为主,货币只占其中一小部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
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
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
四
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
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口都成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
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
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据学者对南宋宝佑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
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
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
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
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
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
五
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
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开始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
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
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
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
也许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国家重商政策对于资本主义之兴起的重要性:宋朝在河北路与京东路实行食盐自由通商制度,在其他地方则推行盐引制(国家间接专卖)。按道理说,食盐的禁榷应该会妨碍民间商品经济的发育,迟滞资本主义的产生,但学者的研究却发现,在宋朝的食盐自由贸易区,“生产技术并无任何进步与创新,生产规模也未见扩大,盐商的资本增殖速度似乎并不快,见不到特富的大盐商”。倒是在推行盐引制的禁榷区,“能够发现生产技术和工艺的明显改进与革新,井盐生产似乎还出现新的生产关系的萌芽,也能在实行钞引制的东南盐区见到发家致富的大盐商”。
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指政府机构被置于天子的直接指挥之下;而不是说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
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惟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
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
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
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
六
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
请注意,这场发生在11~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毫无疑问,并非由西方输入——此刻的西方,还在漫长的中世纪沉睡;而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一个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
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不过,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
文明积累的假说与唐宋变革的历史事实,首先宣告了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荒谬。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
讽刺的是,这类对中华文明的诬蔑式论断,居然获得中国公知式人物的共鸣与赞赏。在中国网络上,还流传一句据称是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名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被无数网友奉为圭臬、一遍遍引用。
然而,如果赫尔德与黑格尔(假如黑格尔确实说过那句“名言”的话)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准确的,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
当然,中西的历史都不可能停滞,西欧历史以他们的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也以自己的轨迹演进,经过漫长的文明冲积,“造极于赵宋之世”,产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们这样的描述,也挑战了费正清先生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
所谓“冲击—回应”理论,简单点说,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然而,当宋王朝在11~13世纪打开近代化的大门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在哪里呢?
七
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远因,我认为,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
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做“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
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
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
“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
“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
“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
“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甚至在观念上,全国臣民都被当成是大汗的奴隶,所谓“普天率土,尽是皇帝之怯怜口”。
“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
“路引制”的恢复。汉唐时,人民如果要出远门,必须先向官方申请通行证,叫做“过所”。宋人则拥有迁徙之自由,不再需要什么“过所”。但元朝又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做“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
“籍没制”的泛滥。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已经很少适用,并严格控制适用,如宋孝宗的一项立法规定:“自今如有依法合行籍没财产人,并须具情犯申提刑司审覆,得报,方许籍没。仍令本司常切觉察,如有违戾,按劾以闻,许人户越诉。”入元后,籍没制度又泛滥起来,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
肉刑与酷刑的制度化。自汉文帝废除肉刑之后,黥(刺面)、劓(割鼻)、刖(斩足)、宫(割势)等肉刑已基本上不用,宋代承五代之旧,保留刺面之刑,但劓、刖、宫一直不敢恢复。元朝则将肉刑入律,如“盗牛马者劓”。陵迟等惨烈的酷刑,在宋代只是法外刑,极少应用,在元朝则正式编入法典,代替绞刑成为元代死刑的两种执行方式之一,陵迟开始泛滥化,致使中国法制出现野蛮化的趋势。
“人殉制”的死灰复燃。人殉作为一种远古的野蛮蒙昧风俗,在汉代以来的中原王朝已经基本消失,只有零星的自愿殉葬。北方的契丹、女真等草原部族还存在着人殉之俗,这应该是社会未完全开化的体现。元朝贵族是否保留人殉,史无记载,但元廷鼓励民间殉葬行为则是毫无疑义的,《元史》载:“大同李文实妻齐氏、河南阎遂妻杨氏、大都潘居敬妻陈氏、王成妻高氏以志节,顺德马奔妻胡闰奴、真定民妻周氏、冀宁民妻魏益红以夫死自缢殉葬,并旌其门。”在这一恶俗中成长的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即恢复人殉之制。
“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
“宵禁”的重现。宋代之前的城市有“宵禁”之制,宋朝时“宵禁”制瓦解,出现了繁华的夜市。但元代又恢复了“宵禁”,入夜之后,禁钟响起,即不准居民出行、饮宴、点灯,“看守之人,巡行街市,视察禁时以后,是否尚有灯火,如有某家灯火未熄,则留符记于门,翌晨传屋主于法官所讯之,若无词可藉,则处罚。若在夜间禁时以后,有人行街中,则加以拘捕,翌晨送至法庭”。
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只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粗鄙治理体系的特点是税率超低,政府只能维持最简陋的形态,用孟子的话说,这叫做“貉道”;以现代的眼光审视,那种简陋的政府根本无法在历史转型期组织社会与经济的革新。
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八
元制的殖入,不仅仅影响于元朝一代,而且改变了后面历史的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诸色户计、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肉刑与酷刑制度、人殉制、海禁制、宵禁制、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
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
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太大的市场与太多的货币,人们基本上自给自足,即便有零星交易,也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连衙门办公的“文具纸张,甚至桌椅板凳、公廨之修理,也是同样零星杂碎的向村民征取”(黄仁宇语)。
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挥,“寸板不许下海!”宋元时期负责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被朱元璋改造成“通夷情、抑奸商,俾法禁有所施”的机构,即接待海外朝贡使团、同时查禁海贾的国家机关。
元廷因为统治技术粗糙,表现出宽纵的特点。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说禁海就禁海,说不许开矿就不得开矿,说廷杖就廷杖,说死罪就死罪。因而,朱元璋时代对于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严厉得多。
明王朝的悲剧便是,它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洪武型体制”,才可能艰难地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近代化轨道上来。到了晚明,随着匠籍制与诸色户计的松懈,月港的开放,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型体制”才宣告解体,繁华的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这一段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
可惜,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清人入关,中世纪制度又出现回潮:
社会经济层面:清初恢复了严厉的海禁,强行将沿海居民内迁五十里;后海禁虽开,但乾隆又改“四口通商”为“单口通商”,又拒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的通商要求;从草原带入奴隶制,“听民人投充旗下为奴”;禁止或限制民间采矿,“一切铜银坑俱封不开”。
文化生活层面:强行剃发易冠,以此强化民间对朝廷的服从;大兴“文字狱”;立碑严禁士子言事论政;大面积禁毁图书,“士民葸慎,凡天文地理言兵言数之书,有一于家惟恐召祸,无问禁与不禁,往往拉杂烧之”,导致知识积累发生断裂,士民思想陷于禁锢;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之后,江南士风出现了严重的奴化。
政治制度层面:清王朝拷贝了朱元璋开创的体制,同时又将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国家的元首,还是日理万机的政府首脑。明朝式的皇权专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关系,致使整套体制显得非常怪诞,也为清末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我们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转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但清朝体制跟君主立宪制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改造起来势必要伤筋动骨,于是主政者拼命拖延,在野者则等得不耐烦,最后一拍两散。
追究起来,这首先应归咎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当上政府首长,等于抽空了“责任内阁”的制度基础。清制因之,设军机处,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与近代“责任内阁”的距离,甚至要远于明代内阁与“责任内阁”的距离。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体下,将宰相领导的政府转换为“责任内阁”,我相信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欧陆启蒙主义思潮的感染,又极不满清王朝应对近代转型的低能,开始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
但他们的思考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作抽丝剥茧,而是直接将炮口对准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构成了近代转型的路障,是传统文化阻止了近代化。
这样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时期全面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达到顶峰,余绪绵延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河殇”症候群。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跪拜在“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脚下。顺乎逻辑地,他们主张以全盘摧毁传统的极端激进方式建立“美丽新世界”。他们控诉传统婚姻家庭,拆毁祠堂,抨击宗族,砸烂孔家店,消灭士绅阶层,挖掘孔子墓,焚烧儒家经书,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造国民性。
然而,他们设想中的“美丽新世界”直到最后,都未能建成。
震荡的一百年过去,中国白了少年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传统了,是时候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