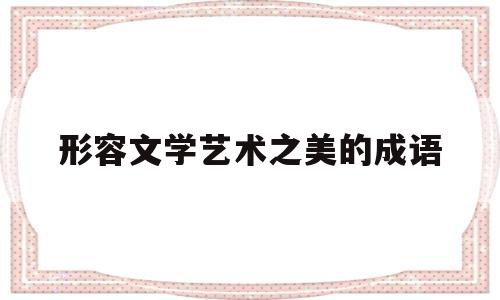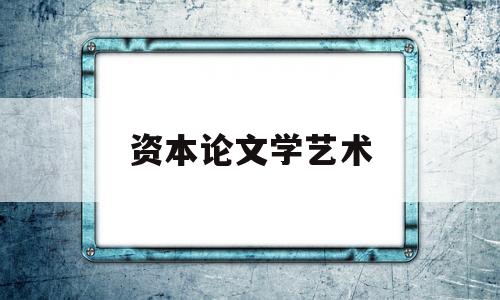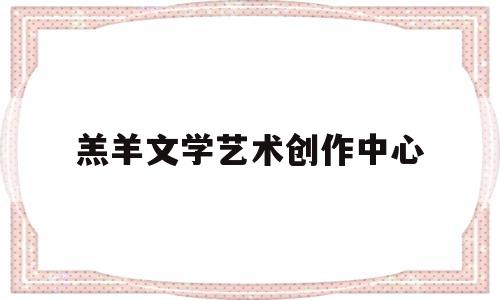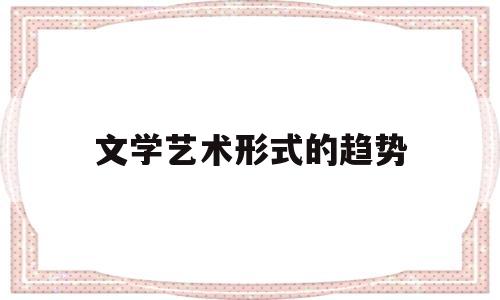杨引丛,男,甘肃省漳县金钟镇人,下肢残疾,初中毕业后自学文学写作,1992年参与组建金钟文学社,任文学双月刊《金钟》主编至今,编印的《金钟》现已出刊到140期。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定西市残疾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会员。
作品欣赏..............
YIN
音
音乐的童年
杨引存
在网上听到一个二胡独奏曲,是那么的熟悉,熟悉的如同碰到了阔别多年的发小,赶紧收藏到音乐盒,反复地听,音乐把我带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那段时间,也就是我刚刚走进小学的时候。
由于身体原因,我上学时已经11岁了,老头子被当时一波紧接着一波的尊师重教热感染,梦想着自己的孩子也能成龙成虎,于是拔苗助长,一进校门就让我报二年级。那时候的课程比较简单,没有现在这么繁重,语文和算术课本都薄薄的,正文的字很大,内容少。母亲在家里教了我一点点数字和汉字,二年级念得不太吃力,玩耍的时间很多,课堂上作业就能完成,一到下课就是疯玩。
中午的这段时间,我们吃过饭,就会三五成群地到村子南边的乔家护林里去,好大好兴旺的一片杂木林,有上百年的古松,有密不透风的柳树,有四处蔓延的沙棘树,还有结着可食用的红色浆果的不知名的灌木,有结紫葡萄那样密密麻麻的小果实的我们当地叫梅棱儿的小矮树......比鲁迅先生一唱三叹的百草园宽阔的多!
同伴们从林子里不光采来大快朵颐的山珍,还会连窝端来有几种颜色的鸟儿的蛋,受了伤的红嘴鸦,毛没张齐的小鹰。我们在乔家护林满载而归时,往往已到了上课的时候。我行走不便,一块的同学们都很仗义,冒着挨骂挨教鞭的风险,也要陪我一块回来。
若是刚刚上课,老师一看我们被树枝划破的衣服和野果染得五眉六道的脸,就知道我们钻林去了,威严却不失幽默地斥骂几声,在其他同学的窃笑中靠墙站半节课,就算惩罚。有时候运气好,是自习课,等我们蹑手蹑脚偷偷挤进厚木板钉的大门,悄悄溜进教室里,校园里飘扬着明快的音乐,从教室的窗户纸望出去,就见北房老师办公室的门敞开着,穿黑色中山装,戴蓝帽子,脸膛红润,络腮胡子,身材胖胖的蔡老师坐在结实的没上过漆、桦树做的靠背椅上,半闭着眼睛,纵情地拉二胡。他不远处是马老师,跷起的二郎腿上蒙着一块手绢,二胡搁在手绢上。他俩对面的李老师操一把板胡,其音恣肆高扬,李老师似乎用了很大的力气,嘴角摆来摆去地,弓弦拉到头,推送之间时而如铁匠轮锤、猎手举枪,时而如大树张凤、虬枝乱舞。三人全然忘怀了是在小小校园,分明是夸骏马奔驰草原,驾扁舟出没江湖。
三位老师如痴如醉演奏的正是我三十余年后再度重逢的这首二胡独奏曲《喜送公粮》!
当时自然不知道这首乐曲的名字,三位老师用毛笔字在整张大的白纸上,将曲谱工工整整抄上去,挂在墙上,反复地演奏。记不清演练了多久,之后的几十年里再无缘聆听这首二胡曲,今年在网上刚一听到就立马想起来,应该那时候老师们演奏的次数很多,把它深深地刻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他们不是要去参赛,也没有谁来布置任务,这是他们那个时代人的娱乐和享受。我很幸运地赶上了激情年代的末班车,在小学的几年,真正是伴着音乐度过的。晚饭后,蒙蒙细雨中,曲老师领着我们几个小鬼往他住的土楼走去的路上,慢悠悠地吹着笛子,笛声传送到很远很远的村庄,传送到那些匆匆赶路的行人耳边。《催马扬鞭运粮忙》、《牧民新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这些曲子都是在那时候走进我的,有一些仅仅是片段,根本就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但是那优美的旋律,深深地植入我的心田。以至于后来再听那些连匠人都算不上的红人们的声乐器乐,怎么都觉得不对劲。
感谢那个物欲尚未横流的时代,感谢那个田园牧歌和昂扬向上结合的时代!
今年春节期间,年过七旬的蔡老师到家里来看望我。老人家精神矍铄,虽然也胖,身材和三十多年前我们上小学时候似乎差不多,耳聪目明,不显老态。我们上学的时候老人家是民办老师,退休的时候也未能转正,听说给儿子们在山里放几年牛羊,山里的好环境加上他的良好心态,才有了这么好的身体。近两年,又进城给孙子陪读做饭,发挥余热。
三人组合里的马老师于前年去世了,尚不到六十岁,无情的病魔夺走了这位好老师的生命。在他去世的前一年,兰州支教的大学生拷给我的相册里有一张他们和马老师的合影,是去马老师家里做家访时拍摄的,亮晶晶的夏日夕阳下,马老师面容清癯,坐在屋檐下的矮凳子上,和同学们在谈心。自然光下过于苍白的脸色预示着他身体的异常,不多久便查出肝癌。这位一辈子不动烟酒,我记得的时候就和药罐子打交道的极爱清洁的老人,除了到学校教书就呆在家里门也不出,像城市里的那些遗世独立的教授,也许是他离世俗的生活太远了,天不假年,及早离开了他的岗位。
我离开小学后,再也没有听到他们拉二胡拉板胡吹笛子,生活在逐渐富裕起来的同时,似乎越来越琐屑,越来越苍白,越来越实际,实际的和他们曾经钟爱的音乐渐行渐远。二胡笛子不知到哪里去了?马老师家里的墙上再没有看见挂着的二胡和笛子。一个秋天阴雨滴沥的午后,我去马老师家,他躺在被子里,半拉窗帘,录音机开到很小,里面放的是陕北民歌。
三位老师里头李老师最年轻,还不到六十吧?他身体很好,记得我们念书那阵子,他可是篮球健将,经常和村上的农民们对垒,几场下来,上课铃声响起的时候,李老师用右手的食指转动着篮球,篮球在他的指头上好像生了根一般飞速旋转却不掉下来。他肩膀上搭着外衣,蒸腾着热气的头上斜挑着帽子,打着口哨走进办公室,跟在身后的我们又佩服又羡慕。
李老师很早就不干民办老师了,后来干过几年村委主任、支书,现在也不干了。我和他离着三十几里路,很少见面,他虽然不干老师了,不干村官了,眉宇间还有着当年的威严和傲骨,我认真观察,从他身上看不出别人失势后的潦倒,萎靡,巴结,颟顸,依然是那股倔强劲,乐观,自信。前年我忽地萌生了要给李老师送一把板胡的念头,两年的时间过去了,此愿未了,但我一定要去了却这桩心愿,就是不知道他老人家还演奏板胡吗?和谁搭伴呢?
屋外,夏天的夜在静悄悄地进行。我坐在电脑前,音箱里放着《喜送公粮》,追忆似水年华,怀念那些在我心灵上留下美好印象的人们!
漳县残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