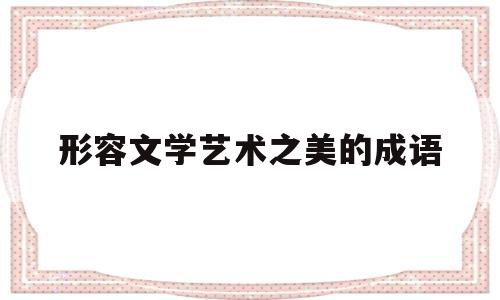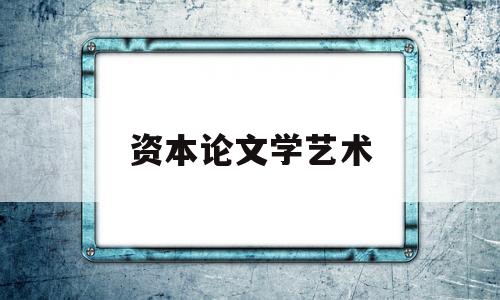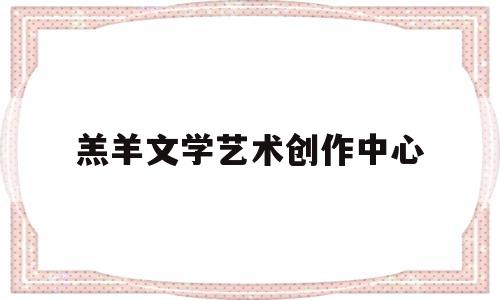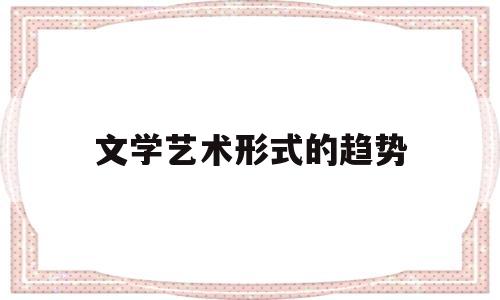按:本文首发于《中国图书评论》2006年第11期,题为《反传统的传统走向终结?》,主要是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热”进行了总结。
新启蒙再续反传统的传统
以“全盘反传统”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对当时现实政治绝望之后寻求突破的一种努力,与之类似,八十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也是在人们反思“文化大革命”中所看到的制度性根源之后,作出的寻求现代化之历史性突破的一次努力。
上世纪八十年代最大的文化热点就是“文化热”。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惟一的不同是,出现了“现代化”的概念。启蒙知识分子主张,现代化首先是人的现代化,须打破落后、专制文化的束缚。但知识分子又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形成的正统文化乃是中国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延续。中国之所以没有建立市场经济,没有实现人的个性自由,总之,之所以没有实现现代化,皆因为“中国文化传统”存在根本性缺陷。因此,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首先实现文化的转型。
因此,整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西文化比较是一大学术热点。而这种中西比较通常会变成古今的比较。比较的基准跟新文化运动时代一样,就是科学与民主。西方就等于科学与民主,因而启蒙知识分子首先在价值上肯定西方为先进的、现代的,而中国则因为缺乏科学与民主而被判定为落后的、非现代化的。中西比较不是出于对中西文明之历史、逻辑知识上的兴趣,而是为了对它们作出价值上的判断,实际上是为了更为细致地发现中国文明的落后之处,从而为制定具体的、细致入微的现代化方案,进行知识上与心理上的准备。很多启蒙知识分子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必须放弃黄土文明,而拥抱蓝色的海洋文明云云。
在启蒙知识分子那里,科学与民主有其特定含义。所谓“民主”实际上是指个人的精神自由,其实质是个性解放。新启蒙运动的主要精神资源来自弗洛伊德、萨特和尼采。他们将知识人的关注点从集体转向了个体,从社会性存在转向了精神的存在。长期处于制度性压抑的人们由此似乎获得了心灵的自由,尼采“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口号则是那个时代很多知识人的抱负。所谓“科学”,其实是科学精神、科学态度,或者就是说唯理主义,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以理性作为惟一的尺度。上世纪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中的唯科学主义主要通过“走向未来丛书”传播。
他们所引入的科学方法主要包括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这些方法突破了当时正统意识形态所提供的历史哲学,不过,它自身也变成了一种“唯科学主义”的新教条,被广泛应用于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各个领域的研究中。比如,金观涛利用系统论研究中国历史而提出中国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之说,此说对于当时之全盘反传统提供了充分的学理依据。
与新文化运动一样,新启蒙运动反传统的初衷未必仅仅是为了进行文化清算,启蒙知识分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所做的是文化事业,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在寻求突破现实的制度困境的历史性出路。应当说,启蒙者所介绍的西方思想资源确实冲击了当时正统的意识形态,从而为市场、法治之发育进行了某种心理与社会层面的准备。但是,把现实的制度问题归因于文化,就像朱学勤先生所说的,“在文化的脂肪上搔痒”,终归是一种方法论上的巨大错误。他们忙于与文化、与民族性作战,反而忽略了对宪政、法治、民主等制度因素的深入思考。
这种错误源于启蒙知识分子对于自由的错误理解。跟新文化运动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新启蒙运动知识分子所接受的乃是哈耶克所说的法国式的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强调理性至上,希望通过摧毁传统,在新文化、新道德、新人性的基础上重组一个新世界。结果当然是适得其反。新文化运动激烈的反传统已经给中国知识界带来了虚无主义,加上政治生态的恶化,社会已经处在道德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八十年代,商业化浪潮已经蠢蠢欲动,新启蒙运动再度借助西方思想资源批判传统,冲击蕴涵于其中的道德和某些社会制度。这确实把人从政治迷信中解放出来了,但也使人不再受任何道德与文化约束,从而使此后的商业化过程急剧地非理性化。
复兴传统的潜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西学热中还有另一股“人文主义”潮流,它主要围绕“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展开,这个知识群体致力于对德法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的译介。
这些思想资源最初也是启蒙的力量,因其在西方脉络中对现代化的反思,经由一种误用,也可以起到批判另一种现实的作用,毕竟,“文化大革命”式的蒙昧和专制其实也是一种现代性。不过另一方面,这些思想流派对于西方现代化的反思与批判本身,也让当时的知识界意识到西学的复杂性,从而稀释了知识界对现代化的价值崇拜,这反过来让部分人士对中国传统另眼相看,其中某些人物更是后来转而对传统采取了一种亲和态度。
因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强烈反传统的文化气氛中,传统其实仍然自有其天地。就在启蒙知识分子通过中西比较而全盘否定传统的时候,在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寻找中国固有传统的努力。新启蒙运动确实有点滑稽:经过几十年的全盘反传统,传统可能早已被摧毁殆尽,部分年轻的文学家觉得,新启蒙运动其实是在跟风车作战。他们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在哪儿?他们要寻文化之“根”,由此形成了“寻根文学”。这些作者具有清醒的反反传统的意识,同时在城市和乡村两个方向探寻民族文化之根。
不过,寻根文学所呈现出的文化却是高度地域性、边缘性的。似乎是对当时的正统文学理念的一种反叛,作者们感兴趣的是城市的市井小民或者边远乡村的未开化的乡民。他们往往抓住某种民俗、习俗,利用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技法刻意进行渲染。他们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的价值判断同样是模糊的,受众的反应也是复杂的,很多人看了张艺谋的电影之后问自己:这是我们的传统吗? 在大陆新启蒙浪潮中真正守护主流传统文化的,应当是“中国文化书院”所代表的一群知识分子及部分活跃于内地的港台新儒家人物。
“中国文化书院”主要由北京大学哲学系一批研究中国哲学和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的学者组成。他们主编的“中国文化书院丛书”显然没有“走向未来丛书”和“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影响大,但在中国文化被否定、被批判的数十年中,却是首次初步地以同情、肯定的态度,介绍、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他们所进行的中西比较研究,也更重视对中国文化自身逻辑的同情理解,而绝不是为了否定。
海外新儒家学说的初步介绍,也在当时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维明。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的文化大讨论中,杜维明在大陆相当活跃。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大陆知识分子对于传统的研究坚持一种外在视角,港台新儒家则采取一种内在视角,这对大陆知识分子是一种全新的理智与情感冲击。港台新儒家学说由此进入大陆,上世纪九十年代大陆的儒学研究热即直接导源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