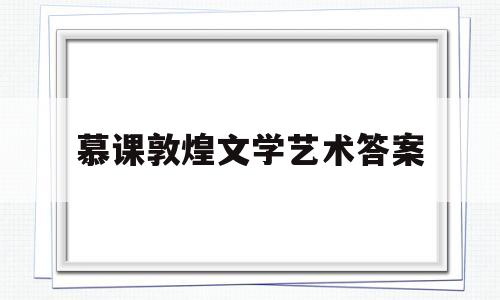对绝望的回应
罗斯·威尔逊/文
路程/译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人们对阿多诺哲学的主要抱怨之一,就是它过于绝望。我已经简要地指出了一些对这种抱怨的回应。但或许阿多诺最广泛的影响正是由于他对纳粹屠杀欧洲犹太人表达了明确的绝望之情。
这些表达对批评家迈克尔·罗斯伯格的著作《创伤的现实主义》(2000)中称之为“再现大屠杀的需要”的讨论产生了巨大影响。罗斯伯格极为强调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名言的影响。(Rothberg 2000:尤其是25,56;又见P:34)罗斯伯格对这种影响的分析很有价值,因为它注意到了对阿多诺这句话的意义的各种阐释。为了纠正在他看来人们对阿多诺这句话的诸多误读,罗斯伯格解读了阿多诺对于诗学可能性和地位的理解,他的观点中有个明显特点。第一,罗斯伯格引用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的话:希特勒给人类施加了一道新的绝对律令,即奥斯维辛绝不能再发生一次(Rothberg 2000:49;又见ND:365)。这种对人们必须避免大屠杀再次发生的要求,正说明阿多诺对纳粹种族屠杀这场灾难的阐释核心是“对未来新关系的必要性”(Rothberg 2000:32)。第二,罗斯伯格强调他称之为“阿多诺诗学中的双重理论”(2000:39)。他的意思是阿多诺固然谴责了艺术的野蛮,它“[再生产了]传统现实主义形式的和谐叙述”,但是另一方面,他坚持艺术应当“[表达]被现实主义压抑了的裂隙”。(Rothberg 2000:40)
通过给阿多诺对奥斯维辛之后诗学的评论建立起更宽阔的哲学背景,罗斯伯格就可以指出人们在接受阿多诺这方面思想的突出例子中所隐含的误读。他集中讨论了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哲学家乔治·斯坦纳的一篇富有影响力的文章(Steiner,1967),以及一篇现代德国文化学者艾瑞克·L.桑特纳撰写的关于战后德国电影的具体研究文章(Santner,1990)。罗斯伯格的解释的长处之一在于他并不是简单地轻视那些他所认为的人们对于阿多诺的误用,相反,他试图展示人们对于阿多诺思想的这些重要运用,不同于阿多诺本人对于奥斯维辛之后艺术的理解。例如,在斯坦纳的解释中,其核心论点是,奥斯维辛只有以资本主义价值观和文化为代价才是可能的。但是阿多诺强调大屠杀是一场内在于西方文化潮流的灾难性加剧,并且它使一种全新的对于未来的态度成为必需,而斯坦纳仍然哀悼一种被理想化构想的文化的逝去,并因此感到怀旧。(Rothberg 2000:31-32)罗斯伯格认为,在斯坦纳的挪用中,阿多诺关于奥斯维辛的思想被导向了过去。
与斯坦纳对资本主义文化的美化相比,桑特纳则将大屠杀作为一种激进和不可避免的与任何过去之事的断裂。像桑特纳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对这种断裂的肯定,显示了它与斯坦纳所渴望的消失的过去具有隐秘的相似之处。两者的预设都是“对于曾经或现存事物的替代怀有一种肯定的眼光”(Rothberg 2000: 33)。当然,两者也都承认大屠杀宣布了与现代性的彻底断裂,这断裂要么将这种肯定性替代置于千里之外,要么开辟了它。阿多诺对于奥斯维辛之后文化的批评,意味着他不会支持上述任何一种立场。首先,他关于和解的观点是否定性的:它不允许任何对于自由社会的明确构想,这个社会最终摆脱了种族大屠杀灾难的可能性。其次,阿多诺并不十分相信,奥斯维辛已经导致了一种与其发生条件的彻底断裂。阿多诺认为,人们并不能明确地说那些情况不再存在了。
阿多诺对人们阐释“大灾难之后的文化”颇有影响,而我这样集中分析罗斯伯格对这种影响的讨论,既是因为它显示了阿多诺影响是多么巨大,也是因为它证明了后续阐释的某些方法已经改变,并且也确实误读了阿多诺的思想。我们可以将罗斯伯格带回阿多诺作品的细节中,将其作为一种更广泛的尝试的例子,这个尝试就是质疑当代评论中的某些主流,它们存在于文学研究中人们对阿多诺的早期接受,以及在对大陆哲学的英语阐释中。尤其是英国文学批评家、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审美意识形态》(1990)中,以及——特别是——美国文学和文化理论家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在其《晚期马克思主义》(1990)中对阿多诺作品的早期接受和适应,最近都受到了深透的审视。罗伯特·胡洛特-肯特可能已经表达了对杰姆逊阐释阿多诺的最强烈的反对。他严厉地批评杰姆逊远离阿多诺的文本细节和微妙差异,并且认为杰姆逊亲自将阿多诺重构沉成了一个可以销售的商品——阿多诺“可能变成我们现在正需要的东西”(Hullot-Kentor 2006:227,引自Jameson1990),这种重构被置于细致的分析中,而这种分析正是杰姆逊对阿多诺的论述中所不具备的。尤其是,他认为杰姆逊对阿多诺的思考方式是完全缺乏同情的。胡洛特-肯特认为,对杰姆逊来说,不能被轻易把握的事物就被弃之一边,只要提到一下,把充满魅力的不可理解性的光芒给予自我提升的审查即可。(Hullot-Kentor 2006:229)
这种流行于早期英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对于阿多诺观点的怀疑态度同样出现在罗伯特·考夫曼那里,他的长篇细致的研究《红色康德》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杰姆逊解读阿多诺如何解读康德的分析。(Kaufman 2000a)在这篇重要文章中,考夫曼尝试了对美学理论的一种彻底刷新。他将杰姆逊对阿多诺的看法,尤其是阿多诺对康德美学的接受(Kaufman 2000:707),作为一种在英语文学批评和理论中的流行趋势的表征,根据这种趋势美学被看作是由于某种原因而在意识形态上妥协了的;也就是说,因为某种原因被遮蔽的虚假设想——关于人类、社会、生产和消费——再也不符合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利益。这个对杰姆逊的分析是与考夫曼有关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并且,也以不同的方式与其他一些人有关,包括贾维斯和伯恩斯坦——这个计划是要在美学遭到攻击和忽略之后,通过其宣称的意识形态批判来恢复美学的名声。对阿多诺的早期评论,其意义是要将他树立在文学理论家的万神殿中,但实际上,阿多诺的著作并不为解释艺术作品提供任何简单可辨的方法;也就是说,很难从中绎出某种判断标准,特别是可以算作“文学理论”的论文学的著作。相反,阿多诺论文学的著作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哲学影响的批评家的著作。(Jarvis 1998:138)
这里需要说明两个重要条件。第一,在这种由解读阿多诺激发的美学复兴中,他对古典哲学美学的接受占有核心地位,但这种复兴并不意味着忽视阿多诺的艺术兴趣中的社会和政治的面向。这种回归阿多诺美学理论的目的——以及证明对阿多诺美学进行直接的政治解读是错误的做法——更是要认出阿多诺思想中真正的重要性的表现,即阿多诺认为艺术作品与当下错误构成的社会具有否定性的关联。
第二,将阿多诺描述成哲学批评家,并不意味着他在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唯一价值是在那些他写的关于具体作家和艺术家的评论中。尽管阿多诺与艺术有关的活动都坚持对具体作品和作品本体的批评,但他的思想激发了人们关于他并未明确讨论过的文学艺术的全新思考,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新思考与他的批判轨迹并不相同。再一次,考夫曼引人注意地将阿多诺带入了与一系列浪漫派作家的对话中,特别是威廉·布莱克(Kaufman 2000b)、珀西·比希·雪莱(Kaufman 2001a)、约翰·济慈(Kaufman 2001b),以及其他美国诗人(Kaufman 2005,又见Gerhardt 2006:73-118)。
J.M.伯恩斯坦的近期著作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这种美学的更新,尤其是来源于登载在《新左派评论》杂志上的关于当今美学政治地位的争论。(参见Beech和Roberts 2002)尽管阿多诺并没有在这些版面上被提及,但他的美学理论在伯恩斯坦的《反对撩人之体:晚期现代主义与绘画的意义》一文中,产生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结果,这篇文章尝试利用对绘画现代性的分析来补充阿多诺本人对于文学和艺术现代性的论述。(Bernstein 2006:11)所以,为了尝试用阿多诺的精神来补充他的写作,这是一项“阿多诺之后”的美学理论的重要发展。特别是,伯恩斯坦认为,艺术已经成为人们对世界的重要感官经验的庇护所,如果不是这个庇护所,这些经验都已经被现代理性摧毁了(Bernstein 2006:7)。所以,他的作品代表了一种严肃思考,即对阿多诺思想赋予艺术作品的意义的思考,以及对现代理性的毁坏状态的思考,这种理性将真实经验驱逐到艺术中寻找庇护。
○●文章选自○●
导读阿多诺
罗斯·威尔逊 |著
路程 |译
拜德雅(Paideia):思的虔诚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品○●○●
“导读”系列衍生的一个图书品牌
拜德雅
长按左侧二维码关注
○ 豆瓣小站和小组 ●
http://site.douban.com/264305/(拜德雅小站)
http://www.douban.com/group/guides/(拜德雅小组)
○●○●
欢迎点击
自定义菜单:“○踪迹●—○拜德雅●笔记簿”
浏览历史文章
欢迎光临官方微店选购